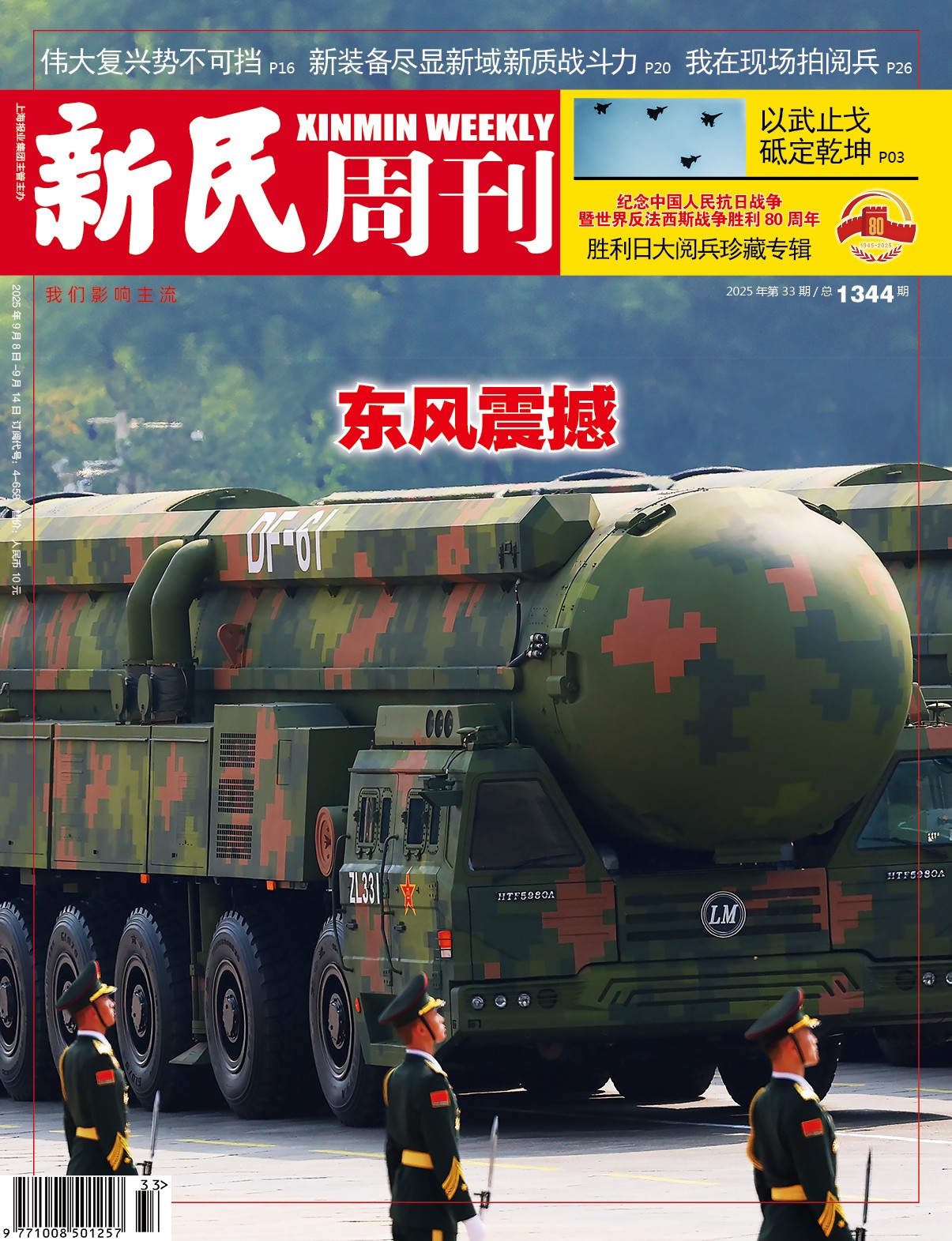从乳名“逃难子”说起
口述|胡真静整理|胡敏
我生于1932年3月,今年已九十有四,是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警。“逃难子”是我的乳名,这个名字是日本侵略中国、突袭上海的残酷见证,也是那个年代百姓颠沛流离的缩影。
1932年1月28日,日本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突袭上海闸北。我第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抗击日寇,沪北地区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近两个月。
当时,我父母居住在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附近,母亲身怀六甲,临近分娩。眼见闸北百姓蜂拥逃至虹口,情势危急,他们不得不舍弃家园,一路南逃至英租界八仙桥,在钟表店楼上的后客堂间暂租栖身。
1932年3月10日这天,母亲乘坐黄包车从虹口返回八仙桥。途中警报骤响,车夫加速狂奔。刚进八仙桥地界,一架日本战机呼啸着掠过头顶,在大世界附近投下炸弹。随着一声震天巨响,车夫惊骇之下松开了车把,黄包车瞬间倾覆!母亲被重重摔倒在地,头上撞出包,手臂划出血,她捂着肚子痛苦哭喊。幸得路人相助,急忙将她送至附近难民所。没过多久,母亲就在那里生下了我。难民们都说我命大,是不幸中的万幸。
父母没读过书,便给我起了“逃难子”这个乳名。它直白、易记,又刻骨铭心——这是逃难中降生的儿子,也承载着对日本侵略者切齿的愤恨。
我尚未满月,母亲就带我回到八仙桥钟表店楼上居住。那时闸北一带的淞沪抗战仍在继续,直到4月底才停火。虹口局势稍稳后,我们一家又搬了回去。为了养家糊口,父亲拉过黄包车,蹬过三轮车,也帮人看守过弄堂;母亲则在蚕丝厂做过女工,开过烟纸店,也当过帮佣。
我开始读书时,用了“胡金生”这个名字。我在有恒私立小学(东余杭路靠近吴淞路)读了四年书。父母为我改名“金生”,寓意我拥有金子般宝贵的生命。是的,我是战火硝烟中的幸运儿,经历了九死一生。尤其父母后来生的两个妹妹,都因患病无钱医治,一个3岁、一个5岁便先后夭折,这让他们更觉“金生”这个名字的珍贵。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虹口成为日寇横行之地。全家生活困顿,饱受欺凌。我读完四年私塾便被迫辍学,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涯。我曾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织布厂当学徒,也在虹口的正昌、永生车行打杂,还帮父亲蹬过三轮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我在位于江苏路的织布厂打工,每日必经静安寺。后来改名胡真静,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
“静”,蕴含着安定、宁静之意。这不仅表达了对日寇带来战乱与贫困的愤恨,更寄托了对太平盛世的深切向往。
解放前夕,我白天打工,晚上到位于四川中路原凯福饭店旁的52民校读夜书。在那里,我有幸结识了地下共产党员周友叶。周长我三五岁,常向我宣讲革命道理,带我去腾凤里(今四川中路572弄)的学校开会,还一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两人保持着单线联系。
上海刚解放,我便遵照周的布置,配合新政府在虹口中学周边(现第一人民医院所在地)收容、登记乞丐和盲流人员,由政府发放遣散费送他们回乡。任务完成后,我便与周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已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万象更新,百业待举。许多单位招工纳贤,我如愿考入公安局。之后在公安战线辛勤耕耘了41个春秋。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