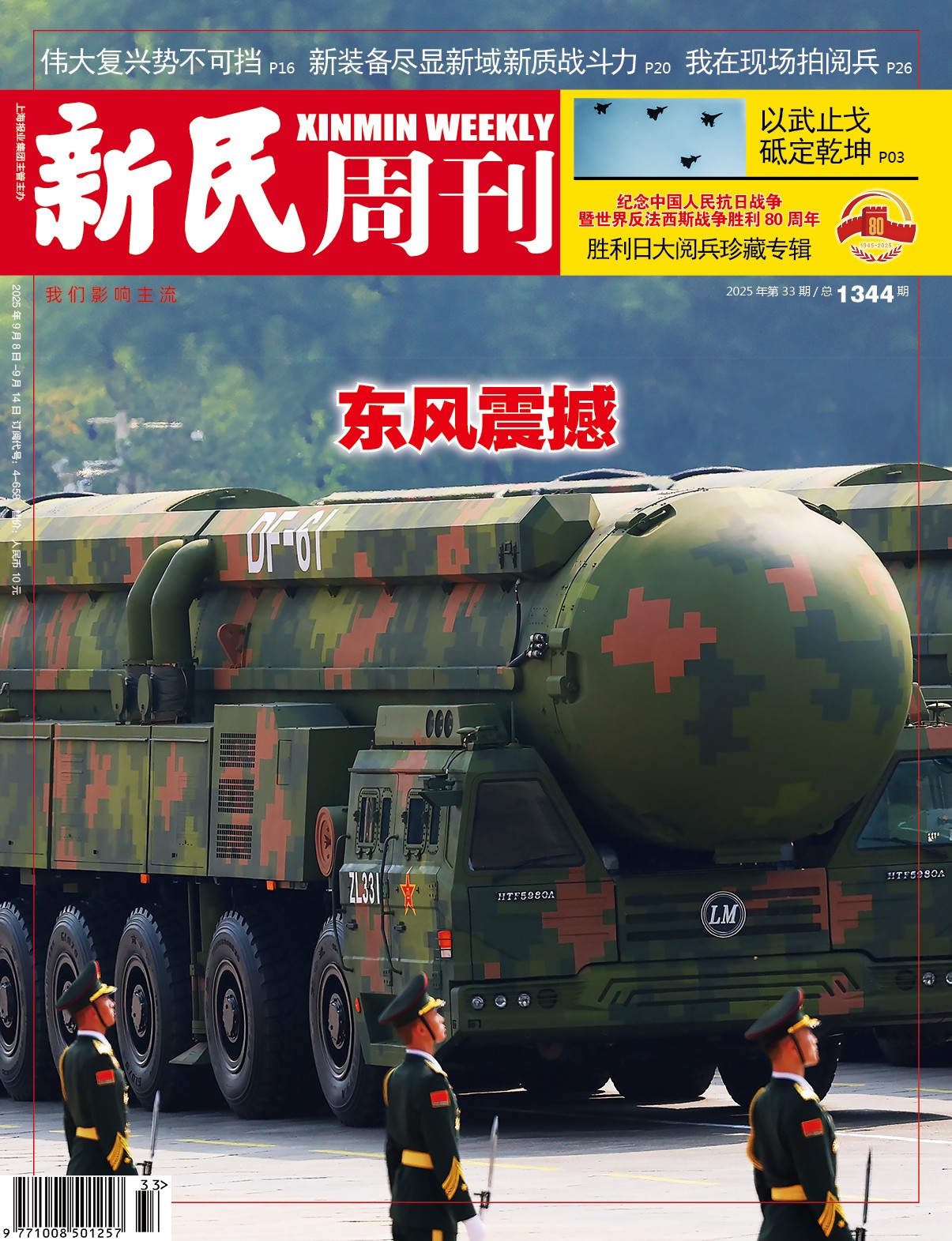1945年:奔向解放区的星夜
口述|赵相如
1944年寒冬,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金沙镇四维中学,我们这群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正经历着压抑的求学生涯。日伪军不时来校“视察”巡逻,耀武扬威,校方被迫将外语课由英语改为日语。校园内乌烟瘴气,令人窒息。
寒假回到南通县西亭镇东北的乡下老家。一天,有人来动员我们去抗日根据地念书。那里是片好地方,念书不收学费,食宿全免,不打人,不骂人,讲民主。于是,我和张维孝下定决心,奔向解放区!
1945年农历正月十七,夕阳西垂时分,我们背起简陋的行囊走出家门,赶到东横车路的孙家土地庙旁。交通员如约而至,带领我们沿小路向东疾行,夜宿农家。领队郑重告知:参加革命,必须改名换姓,既为保密,也为不牵连家人。于是,我改名赵义,钱永昌改名洪平,张维孝改名张勺。队伍中石港来的女青年徐熙,前脚刚离家出走,父母后脚便一路追寻而来。所幸我们安排周密,徐熙始终未被发现。后来得知,她是为了逃避家庭包办婚姻而毅然投身革命。
不久,我们在张家沙集中,开始了长途跋涉。首要难关,是穿越骑岸镇北头伪军和日本鬼子的岗楼附近。队伍拉开距离,三三两两装作路人前行。领队叮嘱:步子要大,但绝不能跑,以免引起敌人警觉。走着走着,鬼子岗楼的轮廓清晰可见,越来越近,甚至能看见钢盔在阳光下反射的刺眼寒光。我们强装镇定,若无其事地快速横穿公路,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
不知走了多少日夜,也不知更换了多少位交通员。一天傍晚,领队严肃地告诉大家:今夜要穿越日伪封锁线。这是敌人为隔绝通(南通)、如(如皋)地区通往解放区而设立的“篱笆墙”,务必万分小心。
夜深了,寒风刺骨,星光黯淡。我们屏住呼吸,悄无声息地摸索前行。渐渐地,一堵望不到尽头的巨大竹篱笆墙横亘眼前。交通员熟练地拉开一个隐蔽的缺口,我们立刻猫下腰,一个接一个敏捷地钻了过去。紧接着,一条宽阔的大河拦住了去路。小划子船分批将我们悄悄送抵北岸。上岸后,队伍急速前进。
突然,“叭!”一声尖锐的枪响划破夜空。所有人瞬间汗毛倒竖,心脏狂跳,冷汗直冒,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哪里打枪?”队伍后面传来压抑的询问。交通员却异常平静地回答:“没事,李堡的鬼子,瞎放枪吓唬人罢了。”他那极其轻松、平淡而镇定的语气,像一剂良药,渐渐抚平了大家的惊恐。
我们在一个“车蓬”(水牛车水处)稍作歇息。此时,东方天际渐渐泛白。当太阳终于跃出地平线时,我们已身处“解放区的天”。终于可以在阳光下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呼吸,感觉脚下的大地真正属于了自己,那份喜悦难以言表。走了一阵,河中一条船上,一位身穿军装、手持步枪的新四军战士映入眼帘——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自己的人民武装。
目的地是靠近海边的东台县三仓。我们先是进入苏中四分区联合中学学习,不久又被选调到四分区会计训练班。
1945年8月15日,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苏中军区四分区报务员朱安庆从电台中率先收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惊天喜讯。他立刻冲到《苏中报》负责人林淡秋身边,满脸通红,激动地报告了这一消息。阮琳听后,抓起一面锣,边敲边高喊:“鬼子投降啰!”消息像长了翅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鞭炮声响彻云霄,庆祝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