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策源地与生力军
在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中,大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和生力军。
上海大学师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运动,组织演讲、示威游行,不惜牺牲生命;光华大学则因五卅运动而诞生,其爱国精神深深植根于师生心中,它的成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收回教育权的一次生动尝试。青年学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筑牢了“爱国爱群”的革命信念。

2025年3月31日,观众在参观“热的血——纪念五卅运动100周年文物史料专题展”。
“五卅运动的策源地”
上海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在五卅运动中,分别担任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妇女团体的领导工作,参与了五卅运动的决策和指挥。
上海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老教授协会会长胡申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以党的领导为例,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蔡和森、恽代英等既是上海大学的教师、五卅运动的领导人,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都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五卅运动爆发时,瞿秋白、邓中夏虽已先后离开上海大学,但由于他们熟悉和了解学校,因而仍然能以党的领导人身份来实际指挥上海大学师生投身五卅运动。蔡和森率先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主张1925年5月30日在租界组织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中共干部的养成所”“五卅运动的策源地”。
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的师生充当了主力和先锋,有400多名学生组织了38个演讲组,在参加示威游行和参加演讲方面,都成为人数最多的学校。在要求老闸捕房释放被捕学生的队伍中,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一直冲在最前列,是第一个被英国巡捕开枪轰击的中国爱国学生,最后英勇牺牲。据他的同学阳翰笙回忆:当时英国巡捕用枪对准他,逼他后退;但他很坚决,说不把被捕学生叫出来,绝不后退。
在参加示威游行之前,上海大学组织了通讯队、救护队和敢死队。上海大学女学生丁郁和黄胤都参加了敢死队。丁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5月29日写下了绝命书:“我死了,请告诉我妈妈一声。”第二天,她将绝命书放在床上就出发了。在整个五卅运动中,公共租界巡捕房抓捕了大批学生,上海大学又是被捕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校。阳翰笙回忆说“‘五卅’运动时几乎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其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许多遭到开除,其中江苏南通、安徽南陵等地被迫离校学生多达一两百人。各地失学青年给上海大学来函,要求免试转学。上海大学支持了这些学生,让他们免试进入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其中就包括安徽学生运动领袖王稼祥。他于1925年8月底来到上海,进入上大附中高三继续他的学业,后来成为中共的卓越领导人。
在创立上海总工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罢”斗争、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五卅惨案真相的过程中,上海大学师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的校名经常出现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上,英国时任首相张伯伦经常发表讲话诬蔑上海大学。1926年,荷兰、英国等组成的关于五卅惨案的“沪案重审三国委员会”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上海大学。诚如上海大学学生周启新所说:上海大学“声震中外,进而成为全国反帝民族运动的中心”。
1933年1月出版的《上海周报·教育史料》第6期刊登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五卅惨案,表面上固是上海八十万劳苦同胞直接向帝国主义者进攻的一幕,实际上能站在最前线的工作同志,可敬可爱的上大学生,确有不可磨灭的助力。上大是中国唯一接受党的熏陶的学校,绝非其他各大学们所可比拟的。……所以首先为国捐躯死于南京路的何秉彝,是上大的学生。领导各队到租界上演讲的多数队长,是上大的学生。捕房拘押援助罢工的大部分人员,亦是上大的学生。五卅时代的上大,上大的影响五卅,中国虽大,实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这是当时社会对上海大学的评价。时任上海大学教授的陈望道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上海大学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
热血青年的革命学校
1925年6月4日,上海租界当局调来全副武装的各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大学,动用武力将上海大学封闭解散。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大学很快就在南市西门方斜路东安里租定18号、29号等房屋为临时校舍。从突遭搜查封闭,到另觅校舍重建学校,恢复教学秩序,前后只有短短两天时间。之后,上海大学一直是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阵地,直至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停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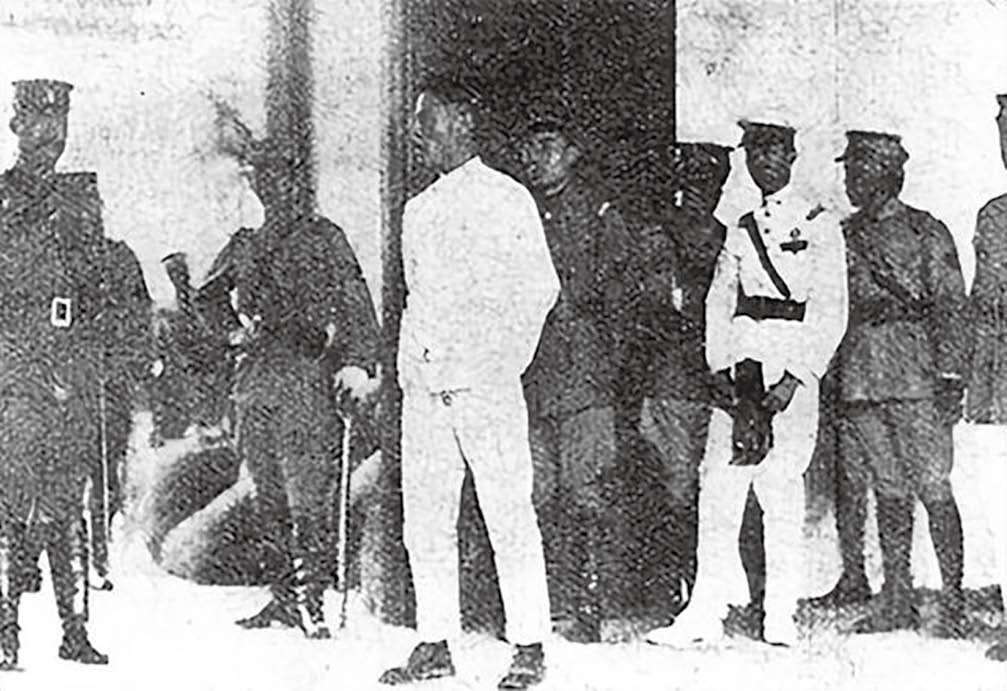
当时上海学生会代表邵华在全皖会馆向奉军讲述五卅惨案的经过。
上海大学何以在五卅运动中起到中坚作用?胡申生表示:这首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息息相关。
1922年10月,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上海大学,于右任担任校长。1923年4月,李大钊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主要负责整个学校的校务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开始接办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知名学者和社会贤达,但师资的主体部分,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党员组成。1923年7月,中共上海大学组成立;1925年2月,中共上海大学支部成立;1926年3月,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成立,直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
上海大学教师张太雷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上海大学另外3名教师任弼时、恽代英、张秋人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上海大学学生贺昌在这次会议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工农部主任。
在五卅运动之前,上海大学师生中已经有大量的党员和团员,党组织在开展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时,也基本上以这些党员和团员为骨干。
上大师生与工人群体的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1924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把沪西工人区列为工作重点,办起了工人夜校和沪西工友俱乐部。上海大学的许多学生参加了两者的筹建,在课余时间,去给工人上课、与他们谈心,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2月,上海大学学生刘华直接领导了“二月罢工”。
“工人顾正红被日商枪击身亡是五卅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而他正是上海大学师生办的工人夜校的学生,和不少上大师生的感情很好。”胡申生说,对顾正红烈士的追悼会、公祭会,上大学生大量参与,展现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上海大学确实是当时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胡申生表示,在五卅运动中牺牲的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1923年从家乡四川彭州来到上海后,最初考进的是大同大学。大同大学当时的学界影响力和硬件条件比上海大学更好,但他读到一半,坚决要转学到上海大学,因为他认为当时只有上海大学能实现他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抱负。那时,像何秉彝一样汇聚在上海大学的热血青年,还有很多。
以上海大学学生为代表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之前经历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然后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而在以工人群体为主体力量的五卅运动中,学生又从工人身上学到很多。在上海大学这样的革命学校中,学生与工人紧密结合后,他们信仰的坚定性、对中国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刻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光华大学的诞生
1925年6月3日晨,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学生为纪念“五卅惨案”死难者,在图书馆前聚集,并下半旗志哀。时任美籍校长卜舫济反对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横蛮扯下国旗,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师生一时群情激愤,中国教职员孟宪承、钱基博等19人、学生张祖培等553人愤而离校。离校师生占到当时圣约翰大学及附中师生的近四分之三,他们坚决地说,绝不再回圣约翰。

1925年光华大学校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图片提供/华东师大档案馆
6月4日,圣约翰大学及附中学生与部分教员发布脱离学校的声明。当时离校学生们商量的结果是,推派代表分两路出发,一路向交通部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请援;一路向圣约翰大学俱乐部请毕业同学刘鸿生出面调解。刘鸿生和南洋大学都拒绝援助离校学生,而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回复说:“我校欢迎你们,只要你们分别考一篇中文作文和一篇英文作文。假如你们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在我校附中。”学生们立即去复旦附中,组成了圣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下午,善后委员会开会,学生王华明报告其父亲王省三答应将其私产用为建立新学校的基地。学生们欢呼雀跃,很快开始筹办新的大学。
1925年6月30日《申报》报道:6月25日,光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6月29日借北京路112号为筹备处;7月4日登报招生。当时,社会贤达王省三、张寿镛等站在师生正义行动一边,襄助离校师生另办新校,并定名“光华大学”。
“光华”两字,出于《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校名同源于此的还有复旦大学。周英才在《光华六三创校杂记》中说:“复旦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从震旦独立出来的;光华是反对美国人卜舫济的压制而从约翰分裂出来的。”当时脱离圣约翰大学去往复旦的,就有后来担任复旦校长的章益。光华大学后来与大夏大学一起,在1951年合并组建为华东师范大学。

1925年9月12日,张寿镛在光华大学霞飞路开学典礼上讲话。图片提供/华东师大档案馆
张寿镛被公推为光华大学首任校长。第一年,就有学生970余人。1926年春,在王省三捐赠的大西路60余亩土地上兴建校舍,秋季建成后学校迁入。
“爱国爱群”写入了光华大学校歌,源于五卅的这种精神在光华大学一直延续。光华大学吸引了鲁迅、胡适、梁实秋等名家大师在校园留下印记。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1927年11月,应光华大学学生会邀请,鲁迅来校作题为《文学与社会》的演讲,回答了“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的问题。他犀利指出:“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造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年11月2日,光华大学校舍被日军焚毁,图书、仪器等损失惨重。学校租借公共租界汉口路证券大楼坚持办学,同时决定在四川设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为避免向汪伪政府登记,上海本部一份为三,文学院改称诚正文学社,理商学院改称格致理商学社,光华附中改为壬午补习社,在教育部注册并颁发光华大学文凭。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恢复办学,次年迁址在虹口欧阳路221、222号校舍办学。成都分部交四川省地方接办,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后发展为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
历史上光华大学办学的旧址,于1951年建起了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如今,旧址仅剩一间286平方米的红砖平房,在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内靠近中山西路校门的位置,被开辟为“校友之家”。
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实际上,除了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另一前身大夏大学也积极参与了五卅运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党史办主任汤涛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大夏大学是最早一批建立“党团合一”的大学。1924年10月,大夏大学学生中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1月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一的党团支部。

1925年6月3日晨,圣约翰学生为哀悼被日本刽子手所杀害的中国工人顾正红以及在南京路上牺牲于英帝国主义者手下的学生群众,在图书馆前降半旗。
1925年5月30日,大夏学生上街宣传工人顾正红被枪杀的情况,有20余人被捕。次日,大夏学生积极参加上海全市举行的罢工、罢市、罢课斗争。6月2日,大夏大学教职员、学生分别发表函电,宣布全体罢课支援五卅运动抗议活动。
大夏师生的爱国举动引起了租界当局的不满,6月4日,工部局发出通知,勒令大夏大学在24小时内迁出英租界。6日,大夏正在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讨论援助工人方法时,英兵突然闯入校内,要求学校立即搬迁,并强行占领了校舍。
校舍被占后,大夏大学临时迁至槟榔路(今安远路)潘家花园继续办学,并函请校董虞洽卿向工部局交涉。14日,《申报》刊载大夏大学学生会消息,表示将另组驻沪代表会,代表全体学生参加五卅运动,并公布具体会务。
汤涛认为,对于大夏大学而言,革命性“与生俱来”。1924年4月,厦门大学发生学潮,当年6月1日,厦大的330余名师生脱离厦大北上上海筹建新校,最初命为“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成为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汤涛认为,当时革命的中心在南方,大夏师生把南方的革命进步思潮带来了上海,并在青年群体中广泛传播。
对于圣约翰大学师生在五卅运动中离校创立光华大学,汤涛认为,其中的动力可以追溯到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发端于北京,收尾在上海,当时在圣约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就已经受到进步思潮的感染,“即使没有成为革命青年,也成为了一个充满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的青年”。
而且,圣约翰大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学生的思想见识超越一般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早已有所觉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开展后,他们的爱国反帝意识进一步被激发。在看到五卅惨案中同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何秉彝等人被列强杀害,同情与悲愤之情必然激涌。

1937年11月,光华大学男生宿舍被炸毁前后对比照片。图片提供/华东师大档案馆
支持光华大学成立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力量:一是进步的士绅阶层,如捐地出资的原圣约翰大学学生的家长王省三、时任沪海道尹的张寿镛等;二是上海的工商业和金融阶层。如实业家荣宗敬、钱永铭、虞恰卿等;三是一批留学美国归来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如余日章、刘湛恩等,他们因为在海外的见闻,爱国的民族情感更加深厚。
另外,20世纪20年代的上半期,中国的教育界大量被外国教会控制。汤涛列举说,据1922年11月《新教育》杂志统计,当时全国教会学校721所,学生33.2万,占全国各级学生总人数的6%强。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无法容忍本国的教育事业大量被外国人控制,因而“收回教育权”的思潮涌动,这也是促成光华大学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五卅”前后达到高潮。1925年12月北洋政府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1926年以后,外国在华所设各级教会学校多数在中国政府立案,改由中国人任校长,并参照中国教育体制作调整。五卅运动,促成了中国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记者|王煜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