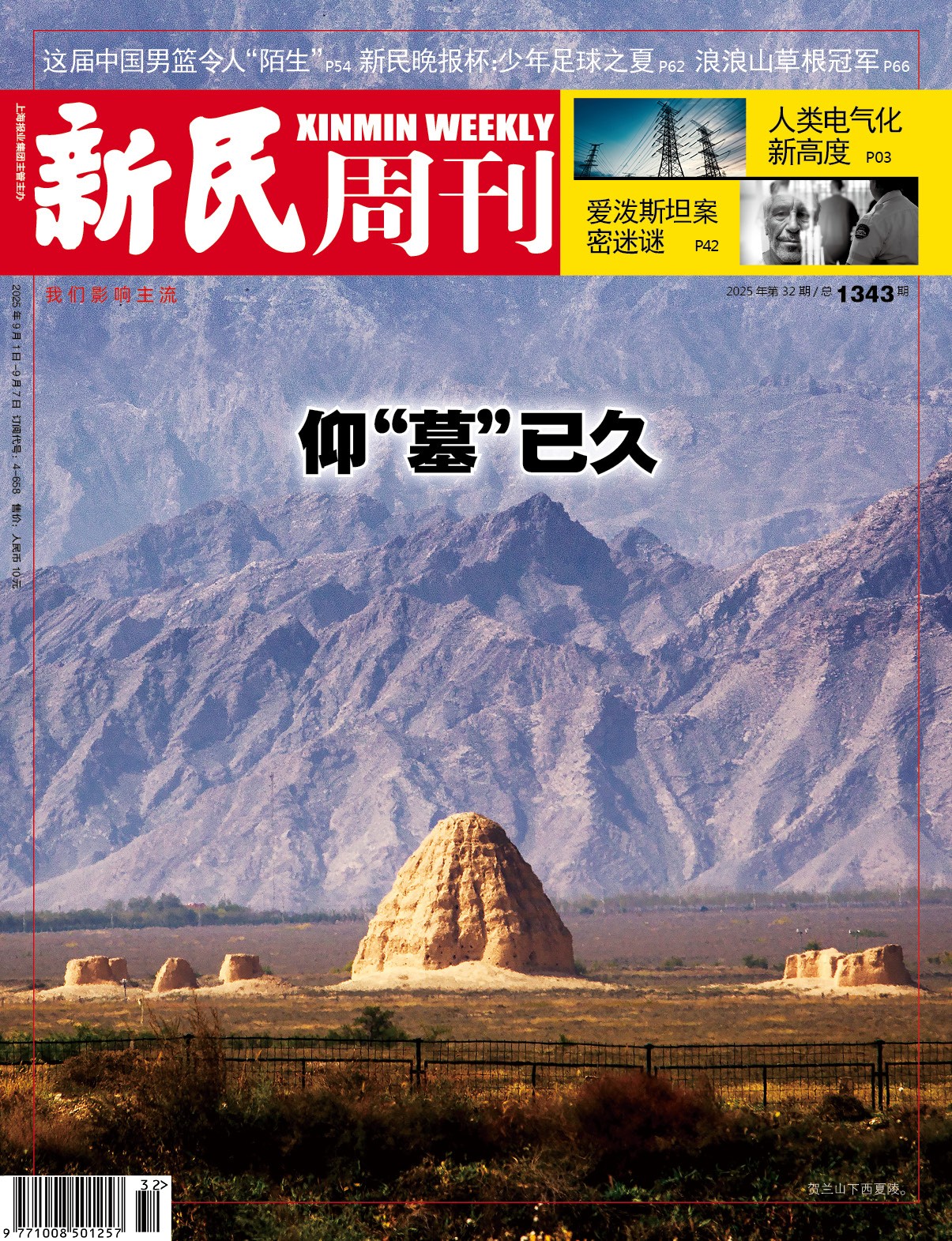“黄肠题凑”再现,大葆台汉墓重新迎客
历经十余年改造,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新馆于2025年5月20日对公众开放。
大葆台汉墓遗址发现于1974年6月,是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的墓葬,是我国发现的第一座拥有完整最高葬制——“黄肠题凑”的西汉诸侯王墓,当时便轰动全国。
作为北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汉代历史文化专题博物馆,它对研究汉代丧葬制度和汉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随着京城文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如今,这里被纳入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成为“一馆三址”中的大葆台遗址馆区,重展幽燕华章。
日前,《新民周刊》记者实地探访了这座雄伟壮观的地下古墓。

自5月20日起,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新馆重新对公众开放。
墓主人是谁?
1974年,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大队大葆台村的两个大土堆,引起了东方红炼油厂(今为燕山石化)的注意,他们想利用这里高凸的地形,深埋几个大型储油罐。开工前,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先来钻探,没想到一个探眼打下去,带出了木头、木炭和白膏泥。
此前在马王堆汉墓的挖掘中,同样发现了木炭、白膏泥,地质勘测处工作人员立马联想到了这一点,随后打电话给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经过考古人员的进一步确认,此处果然是西汉大型木椁墓无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所辖之疆域被后世称为燕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燕国故土置郡县。从此,燕地成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蓟城从先秦时期的一个方国都城转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北方军事重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高祖刘邦意识到,治理国家仅靠郡县制是不够的,因此他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兼取分封、郡县之长,创郡国并行之制。“汉高祖时分封了燕国;汉昭帝时废除燕国,设立广阳郡;汉宣帝时又设立广阳国。”
在考古挖掘中,一件漆器上刻的“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字样,成了考证墓主人身份的关键器物——西汉共有12位燕王,在位24年以上的只有四人:燕康王刘嘉、燕王刘定国、燕剌王刘旦、广阳顷王刘建。墓葬中出土的西汉昭宣时期的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刘嘉死于前151年,刘定国死于前127年,这又将前两位燕王进一步排除。那么,墓主人会是剩下两位燕王中的谁呢?
王岗进一步介绍,刘旦是汉武帝的庶长子,从小被封为燕王,昭帝刘弗陵即位后,刘旦认为自己年长,应当继承帝位,于是便与齐王之子刘泽等策划叛乱。刘旦谋反东窗事发,但因骨肉亲情,并未将之绳之以法。结果后来刘旦二次谋反,燕国直接被汉王朝除名,改设广阳郡,刘旦也自缢身亡。
说到此处,显然,墓主人应该是刘旦之子刘建了。毕竟,汉代最高葬制“黄肠题凑”是不可能出现在因谋反获罪的刘旦墓中的。
刘旦死后,刘建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直到汉宣帝即位,为了政治的需要,恢复了刘建诸侯王的地位,改广阳郡为广阳国,而刘建死后谥号为“广阳顷王”。
这位出身帝王之家,甚至曾有机会登临帝位的刘建,经历了由燕王太子到庶民之身,再到北土诸侯跌宕起伏的一生,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使得刘建的为人处世与父亲刘旦刚好相反,刘建的谥号“顷”字,意为“甄心动惧,敏以敬慎,敏以敬顺”,即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安分守己,这表明他一生都保持着谨小慎微的态度。
神秘的“黄肠题凑”

大葆台汉墓一号墓展区完整展示了汉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葬制。摄影/周洁
大葆台汉墓是广阳顷王刘建与其王后的合葬墓,一号墓主人为刘建,二号墓主人为其王后。墓室的中心是梓宫、便房和“黄肠题凑”。走入大葆台遗址馆区,一股凉意扑面,走进后似乎还能闻见松柏木特有的香味。时值暑假,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一名来自江西的游客就表示,此次他赴京是专程来看墓葬中的“黄肠题凑”。
在广阳王生活的西汉时代,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事死如生的丧葬礼仪,在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中不断趋于复杂而隆重,而“黄肠题凑”,正是西汉最高等级的墓葬制度。
时间回到1974年,考古发掘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随着封土清运结束,考古人员开始正式发掘墓室,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惊喜:一根又一根90厘米×10厘米×10厘米的条木,整整齐齐地层层垒起,堆成了墓室的四壁。每根条木都很光滑,平整划一,不少木材尚坚硬如新,有的表面还有一层黄色树脂油,各条木之间无榫卯固定,却堆垒得十分坚固。其中三面墙壁倒塌严重,唯有西面靠近西北角的一段保存最为完好,木条足有27层,堆成的木墙残高2.67米。
“当时一开始出现这种埋葬形式的时候,在全国都引起轰动,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王岗曾和参与大葆台汉墓发掘的考古学家于杰交谈,他也是第一个将其与“黄肠题凑”关联起来的文物专家。于杰翻阅了大量资料后,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受到启发,第一个明确提出,条木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虽有文献记载,但其真面目如何,一直非常神秘,部分历史学家还常把“题凑”混同于椁室。《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黄肠题凑”一词。三国时魏人苏林曾对其进行注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直到1974年大葆台汉墓的出现,它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呈现于世人之前。
“黄肠”即去皮后的柏木条。因为柏木心是黄色的,切割成长条状后,宛如一根根黄色的肠子。“题凑”即把切割成长条状的柏木条,端头向内码放在一起。
为什么要用柏木呢?一般认为有四个原因。

“黄肠题凑”所用的柏木条。摄影/周洁
第一,柏树生长周期长,且是名贵木材,多用于木椁、庙宇、殿堂、庭院等处;第二,柏木剥皮后呈黄色,颜色高贵,可显示墓主身份地位;第三,柏木材质优良,坚固耐用,经久不坏,耐水湿,抗腐性强,有香气,可以起到防土侵、防水患、防霉变、防虫蛀的作用;第四,相传柏木可以驱邪。采用“题凑”的结构方式,主要是为了墓室的坚固,因为这种结构可以有效缓解封土堆对棺椁的压力。
当然,“黄肠题凑”其实指的是整个葬制,还包括遗体停放的区域“梓宫”(用梓木制作的棺椁),代表活动空间的“便房”(墓主人灵魂休息的地方,位于墓室前半部分)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阳顷王的梓宫共有五重,形成三棺二椁的格局,符合周礼中“天子享七重棺椁,诸侯五重,大夫三重”的规定。事实上,大葆台汉墓的结构是相当清晰且严谨的,严格遵循等级规制,从柏木枋选材到堆砌方式,均与文献记载及葬制规范高度契合,是西汉礼制体系在丧葬领域的直观体现,深刻体现了西汉社会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结构与等级秩序。
这样高规格的丧葬模式,也彰显着墓主人地位的尊贵。据了解,要建造大葆台汉墓中这样一个“黄肠题凑”的“木墙”,总共需要消耗一万五千多根柏木,相当于一片森林那么多的柏树。黄柏木的数量有限且生长周期长,如此规模,也只有身份尊贵之人才能享受。比如老山汉墓的“黄肠题凑”,只在墓门使用了柏木,墓室里使用的是栗木等杂木;江苏发现的西汉广陵王刘胥夫妇合葬的天山汉墓,使用的虽是更为珍贵的金丝楠木,但它并不是“黄肠”,因为只有黄色柏木芯才能叫“黄肠”。

大葆台汉墓中展示的西汉车马殉葬遗迹。摄影/周洁
古墓中寻找城市记忆
由于西汉贵族大多被厚葬,因此一直被历代盗墓贼光顾,大葆台汉墓也遭到过多次洗劫,被盗走了金缕玉衣和大量随葬品。墓主人的尸体,也被盗墓贼“折腾”得一半在棺内一半在棺外,脖子上还套着一段麻绳,直至千年之后,才被考古人员发现。
两千年的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大葆台遗址的发现,丰富着人们对北京地区汉代社会生活、物质文化、思想信仰等方面的认知。古墓的挖掘与探索,能够激发世人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也是现代人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正所谓“知来路,明去路,方能致远”。
作为中国十大古都之一,北京的古墓资源非常丰富。王岗介绍,除了大葆台汉墓外,北京还有燕国国君墓地、老山汉墓、金代皇陵等,还有世界上保存较完整的陵墓建筑和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明十三陵。
其中北京金代皇陵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的“一个缺环”。
历经5代金朝皇帝的60年营建,大房山一带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这里占地超过6.5平方公里、埋葬了17位皇帝以及多位皇族成员。元代散曲家冯子振的“道陵前夕照苍茫”,说的就是此地最富丽堂皇的一座帝陵——金章宗的道陵。
王岗告诉记者,虽然金中都作为一国都城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仍然给北京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划时代的意义。后来蒙古军队攻占金中都城,忽必烈在金中都旧城东北建立起了元大都,而元大都的营建为明代北京城奠定了基础。“明代末期,为了镇住金人风水,明熹宗朱由校两次下令捣毁金陵。直到清朝入关以后,才对金陵做了一定修复,虽然未能恢复往日的气势,但仍为研究金代石刻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明十三陵因明成祖朱棣及其以后共计13位皇帝的陵墓建在这里而得名,其中定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采用科学考古方法主动发掘的皇陵,在出土大量稀世珍宝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教训,比如丝织品出土后受条件所限没有保护好等,这些问题也促成了此后中国文物考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基本方针。而定陵中出土的明代孝端皇后的凤冠,真品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去年根据其设计的国博凤冠冰箱贴销量突破百万件,成为文创“天花板”,明十三陵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记者了解到,明十三陵陵寝正开展新一轮修缮保护,预计到2030年实现明十三陵主体陵寝全部开放,人们将有机会进一步感受到十三陵的明代风华。
岁月不居,春秋有序。当游客们走在墓葬遗址中,总能轻易感受到时空变化带来的古今交叠之感,古墓中珍藏着历史的记忆,也将见证更加绚丽的文化盛景。记者|周洁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