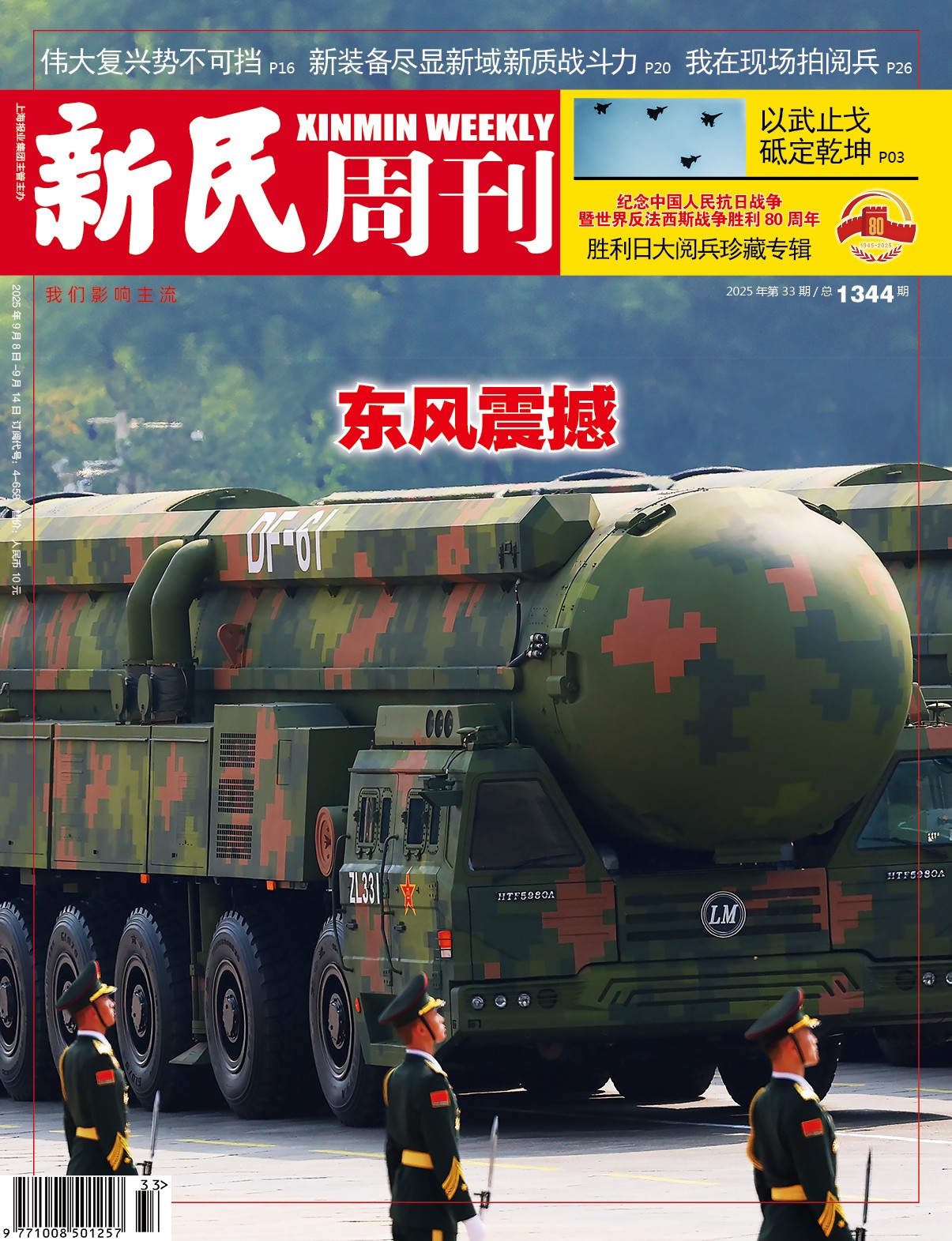上海抗战,不仅“八一三”
“上海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但在上海抗战史的书写中,以往多偏重于市区里的救亡运动、治疗伤兵、救济难民、组织投军、特工战以及工人运动等,对城市外围的活动关注得相对较少。” 8月28日,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闵行区委宣传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座谈会上,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马军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此表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提及上海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总是无法被忘却。然而,还要看到,上海抗战,不仅有八一三。在如今的上海行政区划内,许多地方的抗战篇章,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部不朽史诗的组成部分。
在如今的上海郊区——彼时仍隶属于江苏省的上海县、嘉定县、宝山县、松江县、金山县、青浦县、奉贤县、南汇县、川沙县及崇明县等10个县(1958年划归上海市),英勇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伏击日伪军、破坏交通线、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和支援抗战,展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淞沪支队纵横浦东,显示了游击健儿在沪郊保卫家园、主动出击的英勇斗争精神。
党的领导:上海郊县抗战的坚强核心
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引领与组织保障。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韩洪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中共中央对上海郊县的斗争高度重视,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应上海党组织要求,专门委派张爱萍率领4名师级军事干部到上海,负责开辟江浙地区敌后农村抗日游击斗争。
张爱萍一行从延安出发途经南京时,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指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辟游击战。1938年5月,毛泽东指出:“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方面。”中央书记处随即致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省委当前的中心任务,应是加强对于农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根据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又多次对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新四军在苏南和浙东开辟根据地等作出过具体指导。
韩洪泉说,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在中共江苏省军委、江苏省外县工委、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和江南区委、浙东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崇明县后改隶苏中区委领导),依组织领导关系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
1937年8月至1937年12月,是中共江苏省军事运动委员会(简称军委)领导时期。张爱萍等人于8月下旬抵沪后,奉命成立了军委,张爱萍任书记,后又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开辟江浙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以保证上海失守后军委领导能迁至上海郊县指挥江浙抗日游击战争。11月初江苏省委重建后,仍下设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及委员不变。同月中旬,张爱萍等奉调赴内地工作,江苏省委军委及外县工委工作结束。
1938年春至1940年5月,是江苏省外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外县工委)领导时期。外县工委由沙文汉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外围地区农村各级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和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开辟工作,特别是按照江苏省委“把开拓农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的指示要求,“把大部分领导力量转移到敌后游击战争方面去”,“以群众抗日武装为主,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以星火燎原之势掀起了郊县抗日武装斗争的高潮。
1940年5月至1942年7月,是新四军东路军政会和江南区委领导时期。党中央和东南局鉴于江南敌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划归新四军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并对其组织领导机构和武装力量进行了相应调整,主要由淞沪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浦东、浦西抗日游击区的工作。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成立谭震林为书记的江南区委,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路南特委,直属区委领导。同年10月江南区委随新四军6师北上后,路南特委的工作转由苏中区党委代管。
1942年7月至1945年8月,是浙东区委领导时期。根据中央开辟浙东根据地的指示,华中局决定路南特委划归浙东区委领导,并改组为浦东地委,下辖浦东、浦南、浦西、嘉定及浙江海北地区。1944年11月,浦东地委改组为淞沪地委,下辖浦东、青东、松江、昆南、嘉定、浦南、吴江7个县级工委,并相继在各县区成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坚持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区域抗争:郊野大地上的浴血坚守

上海华漕抗战史迹陈列馆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的活动。摄影/陈冰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宣传发动当地民众,成功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的抗日民众武装与敌伪顽军周旋,浴血奋战,开辟了浦东、青东、嘉定西乡以及崇明等四个抗日游击区。
华漕地处当时的交通要塞,其北侧的苏州河是阻挡日军从北面及西面进攻上海市区的天然屏障。因此,守卫苏州河南岸华漕段防线,对于迟滞日军进攻具有关键意义。
1937年10月,由中共上海组织直接领导的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奉命驻守苏州河南岸。这支队伍在此与日军发生了激烈交火,成功阻击了日军企图渡河南下的进攻。为彻底阻断日军进军路线,中国军队炸毁了横跨苏州河连接华漕与青浦的交通要道——浜北桥。这一行动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推进速度,为后方布防争取了宝贵时间。
作为上海市首个街镇级抗战纪念馆,2024年12月13日开馆的华漕抗战史迹陈列馆以“微观视角”还原了这段历史——通过地方志、组织史及亲历者的口述,让“家门口的抗战”不再遥远,更确认了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全民族抗战初期上海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武装”的历史地位,填补了上海早期抗日武装斗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
8月28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奉贤区烈士事迹陈列馆暨新四军淞沪支队陈列馆正式揭幕。新四军淞沪支队陈列馆展示了淞沪支队等武装在上海郊区开展的汇角战斗、北宋突围战、朱家店伏击战26次重要战斗和53位淞沪支队指战员的光辉事迹。
淞沪支队纵横浦东,最经典的一战,是1944年8月21日的朱家店大捷。淞沪支队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到一个小时歼敌34人,耀武扬威的佩刀队长当场被击毙。这是淞沪支队一次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对当地日伪政权震动极大。日伪放弃了不少小的据点,龟缩在大的城镇,没人敢再下乡扫荡。
“当敌人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不是单纯地退却,也不是与敌人对峙硬拼,而是从侧面、背后向敌人的薄弱环节发起进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我们称之‘敌进我进’。”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在其回忆录《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中用这四个字总结沪郊抗日游击战的战术,显示了游击健儿在沪郊保卫家园、主动出击的英勇斗争精神。
在青东,顾复生辞去米厂工作,与林锡浦、顾若樵等二十多名热血青年,在观音堂组织起了“抗敌后援会”,并建立短枪队。其后,又聚集起徐有基、康松山、曹国祥等农运骨干,组建“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

青东抗日游击区中心观音堂镇一角。
1938年8月13日,顾复生决定切断日寇扫荡、运送物资、调动兵力的主要交通线——青沪公路。深夜,一声令下,从老宅附近的十八号桥到赵巷的八号桥,同时点火。顷刻间,数十公里的公路,仿若一条烈焰腾腾的火龙,将敌人的运输线成功切断。这次战斗,让日军运输线七天没法用,沉重打击了日寇的气焰。
与此同时,在嘉定,吕炳奎花钱买枪,凭借行医时积累的威望与人脉,成为“杨甸民众自卫队”的带头人。在1938年8月13日的当夜,嘉定北门至西门一线城外突然枪声大作,这是吕炳奎部队和西乡民众自卫队率外冈民众向城内示威。1938年9月,邱生凡受党的委托与吕炳奎会面。党组织还安排吕炳奎参观当时有“孤岛上的解放区”之称的难民收容所,并动员上海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前去参加部队。10月,外冈游击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郊县三支主要抗日武装之一。
在金山,日军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当地民众奋起反抗。李新民组织起一支抗日救国自卫团,积极联络金山其他游击武装,最终组成了一支200余人的抗日队伍,屡屡袭击日军。
崇明岛自1938年3月18日沦陷后,始终处于日军的严密控制中,但岛上民众的抗日斗志从未熄灭。1938年,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成立,在中共领导下开展游击斗争,中队长蒋煊洲便是典型代表——这位20多岁的青年率领队员与日军周旋,作战勇敢,被人称为“蒋扑命”。日本侵略军对他恨之入骨,曾多次通缉,两次焚其房屋,砸毁其全部家具。1939年8月,蒋煊洲奉令率部开赴小竖河,打击通敌叛变之杂牌部队。战斗结束后,留下负责降兵改编工作。8月20日,突遭200余名日伪军袭击。蒋煊洲带病率领数名战士掩护部队突围,与敌人血战到弹尽枪毁,最后壮烈牺牲。

上海华漕镇的年轻人用青春之声讲述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以及侯伯泉、赵季昌等烈士的事迹,在抗战史迹陈列馆开启了一场跨越88年的对话。
上海郊县抗战的独特价值
从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上海郊县的武装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条件极为艰苦,但广大游击战士在这座亚洲最大城市的周边,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自始至终表达了上海人民、中国人民不愿做奴隶的信心和决心。
上海郊县的抗战,虽无正面战场的宏大叙事,却以“敌后游击”的独特方式,为全国抗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战略配合到资源支援,从统战实践到精神传承,这些郊野大地上的斗争,深刻诠释了“人民战争”的真谛。
马军表示,上海郊县的抗日斗争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它能够充分反映中共领导上海抗战的一以贯之,揭示各县乡敌、伪、顽、我力量的复杂交错,也能够显现那一时期市、郊两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各种互动,以及上海市、郊与安徽、苏北、苏南、浙东等大江南北地区的彼此联系。
“最近,我整理发表了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的前辈们,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对若干游击队员所做的口述采访,其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我个人以为,加强对郊县抗日的研究,应当是今后上海抗战史学界和方志界重要的延伸性方向之一。”
烽火虽已远去,但上海郊县的抗战史,早已沉淀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基因。记者|陈冰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