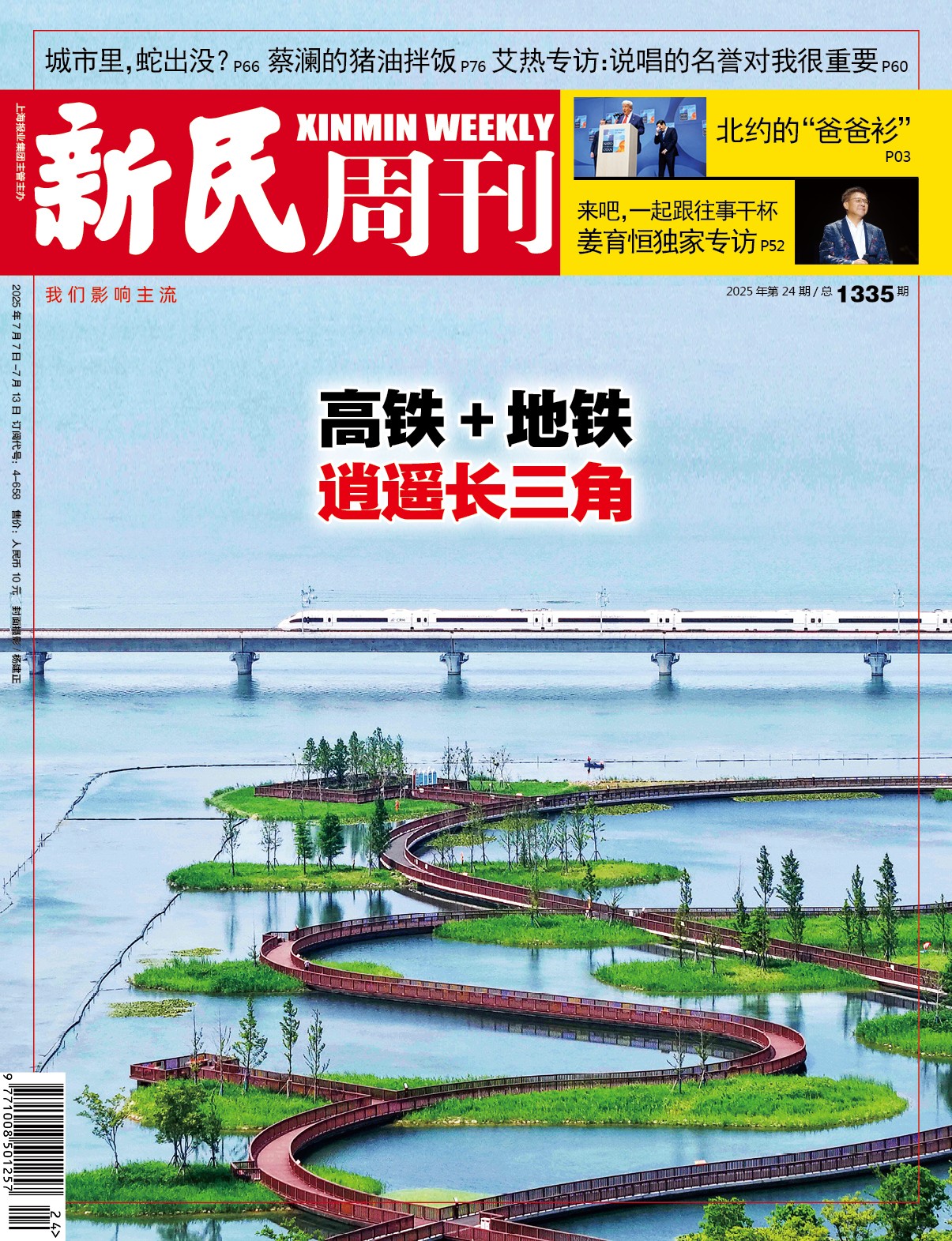雅俗刍议
大抵从事艺术的人,其作品总怕被人指为“俗气”,这是相对“雅”而言的。所谓“雅”,《诗经》六义之一,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本义指鸟,且指秦地之鸟,雅声便代表秦地之声,即王畿之声,使得“雅”字从此被赋予正规和高级的特质。至于“俗”,《释名》诠释为“欲也,俗人之所欲也”;《文心雕龙》说“雅俗异势”,体现为小众与大众、文与野、脱俗与落俗等差池。
切莫以为“俗”总处在“雅”的下风,它的传承力远比“雅”强得多。举凡习俗、风俗都有长期不竭的沉淀效应,且根植于人们的审美认知之中。如大儒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所说:“存诸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这个“狭”字,在这里可解释为“不登大雅之堂”,却非常接地气且富生命力。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汉书》也提到“习惯成,民礼俗矣”。如果去到各地的古村僻壤,当知“风俗习惯”乃世代相传,根深蒂固;“高雅脱俗”如阳春白雪,难摹其形,难追其神。真不敢小看一个“俗”字,它的背后,是几千年历史的积淀。即便“正史”从不正眼瞧它,可一路走来,代表雅正的“正史”越发孤独,体现通俗和演义的“野史”却渗透力极强,流传既广且久。
或为调和雅俗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耳畔,又传来“雅俗共赏”“大俗大雅”“不俗自雅”等圆融的方便说。我也提醒自己,在鉴赏或欣赏别人作品时,不要光从“雅俗”找切入点而不及其余。“俗”字一出口,便“着了相”,且伤人,再说谁又能真正“免俗”呢?站在不同的审美层次看问题,便知俗既俗,雅就一定“雅”吗?仇英技法全面,刻画工谨,有人说他俗;倪瓒简笔折带,惜墨如金,有人说他雅。此说雅,彼说俗,往往说的不是一回事。如果说“雅”字带有褒义,那么“俗”字未见得全是贬义,比如去各地采风,能说有体验价值的“民俗”就是含贬义的词汇吗?白居易的诗常被指为“俚俗”,但其深入浅出、晓畅明白的风格,仍不失大美大雅的一面。如果“雅”常常被证伪,非但俗气,还不是一般的俗。至于雅俗共赏的“俗”必非“恶俗”和“庸俗”,否则何以兼容、怎能“共赏”呢?而“俗美”一词,偏中性,美是美了,却稍带“媚俗”之意了。
儒道两家对雅俗的认知也有所不同,儒家强调“教化”,道家不排斥“从俗”。前者提倡移风易俗;后者宣称“从其俗”再“脱其俗”。一种代表了“雅文化”;一种不忌讳与世俗为伍。因为道家认识到人常常受制于环境而无所作为,却无碍与天地精神共往来。如此说来,“从俗”是韬晦;“脱俗”才见真章,试问:何俗之有?撰稿|喻军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