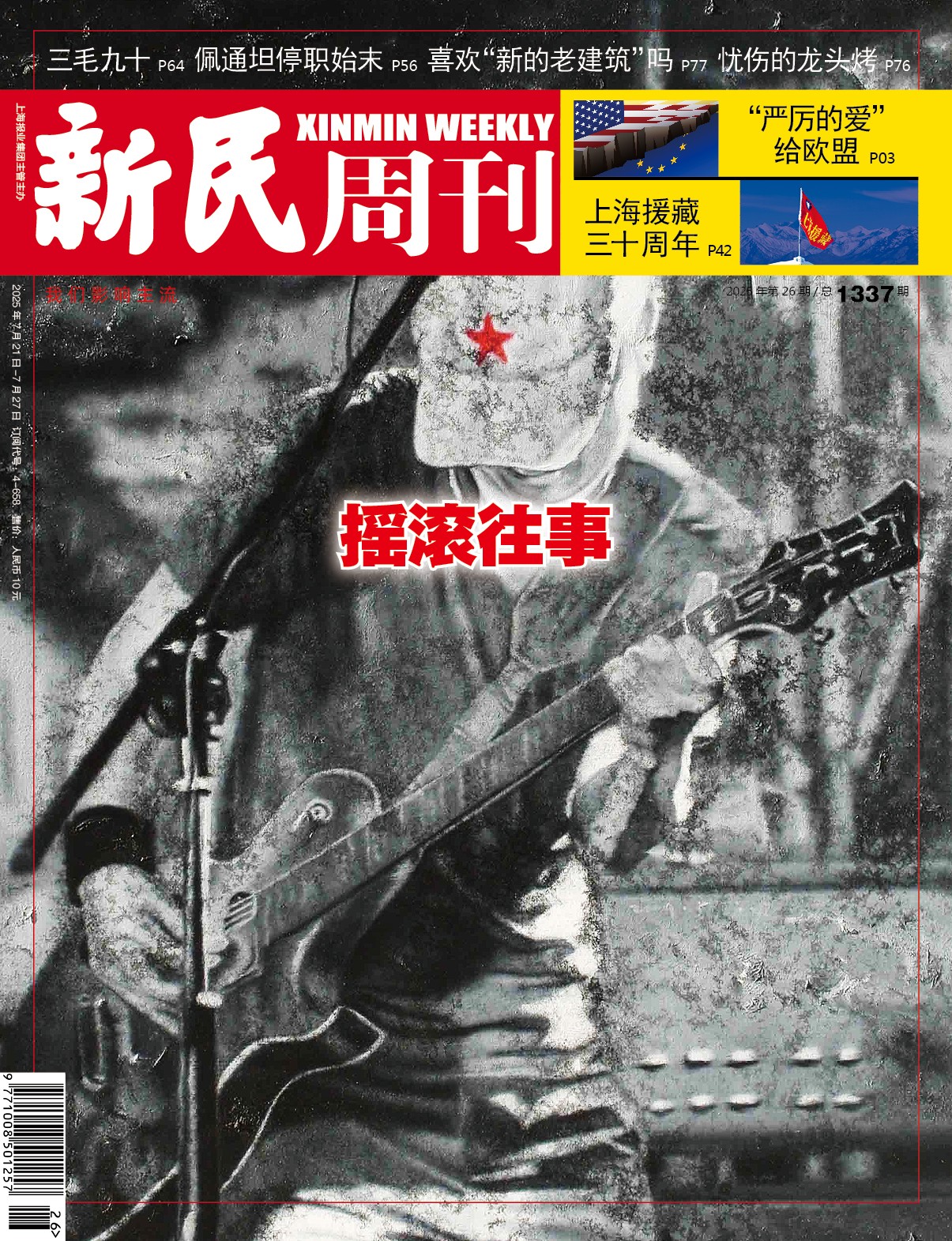谥号与身份之争的背后
青年学者尤淑君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的皇权重塑》所聚焦的历史事件,并非战场上惊心动魄的厮杀,亦非天灾、内乱、瘟疫,不是精细到日常的微观史、心态史,也不是冰冷到丧失人情的宏观史、制度史,但正如作者所言,发生在嘉靖一朝初期的“大礼议”事件,乃是明代政治文化中隐秘且关键的转捩点。这一事件,彻底打破了皇帝与群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为嘉靖一朝嗣后日益恶化的君臣互相猜忌的政治生态埋下祸根。
而所谓“大礼议”,其所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嘉靖帝朱厚熜的身份。当明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六年,即公元1621年卒于豹房时,他并没有留下子嗣。藩王出身,时年15岁的朱厚熜,因此得以入继大统。但为了在礼法上名正言顺,内阁与礼部认为,朱厚熜应该被过继给武宗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成为武宗的兄弟,以符合《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继位法则。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嘉靖的亲生父母,将变成他礼法上的叔婶。支持这一派观点的臣僚,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代表,他们援引宋代濮议案的先例,其观点被称为濮议论。反对者,如礼部观政进士张璁则指出,濮议论不合人情,会使嘉靖“自绝其父母之义”,他们的观点,则被称为人情论。
起初,嘉靖一再恳求坚持濮议论的三位阁臣杨廷和、毛纪、蒋冕让步,不惜重金贿赂其改变观点。然而对这些以清流自许的臣僚,此举只能适得其反。杨廷和甚至以辞官相要挟,逼迫嘉靖接受濮议论。皇帝虽暂时妥协,却在羽翼丰满后,直接下令将已故生父从“兴献帝”升格为“献皇帝”,列于太庙,庙号睿宗,世受香火。大礼议绵延了24年,最后以皇权的彻底胜利告终。兴献王与嘉靖的身份,成为让此后明代诸帝无比尴尬的历史遗留问题。
大礼议之后,君臣关系的濒临破裂,使得嘉靖不得不扩张内阁首辅的权力,让其充当缓冲器与挡箭牌,而首辅始终是皇帝的私臣,自然无法取信于众臣,如同过去的宰相一般成为众臣之首,他需要逢迎上意,因此无法制约日渐集中化的皇权。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明代的制度构建,就天然缺乏对皇权的约束,唯一能规范皇帝的,即是礼法。但当嘉靖出于人情之思,随意更动礼法时,这一唯一的约束也摇摇欲坠,国家彻底成为了皇帝的私产,继而,如此庞大的权力造成了嘉靖自私、精明、虚伪且好大喜功的政治性格。皇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未如此显豁地呈现出来,朝廷内部的政治冲突也从未如此激烈、致命,且具有零和博弈的不可调和性。是以,大礼议应当被视为近代前夜的一次关键历史事件,被细细剖开,一遍又一遍地重读。撰稿|谈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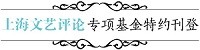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