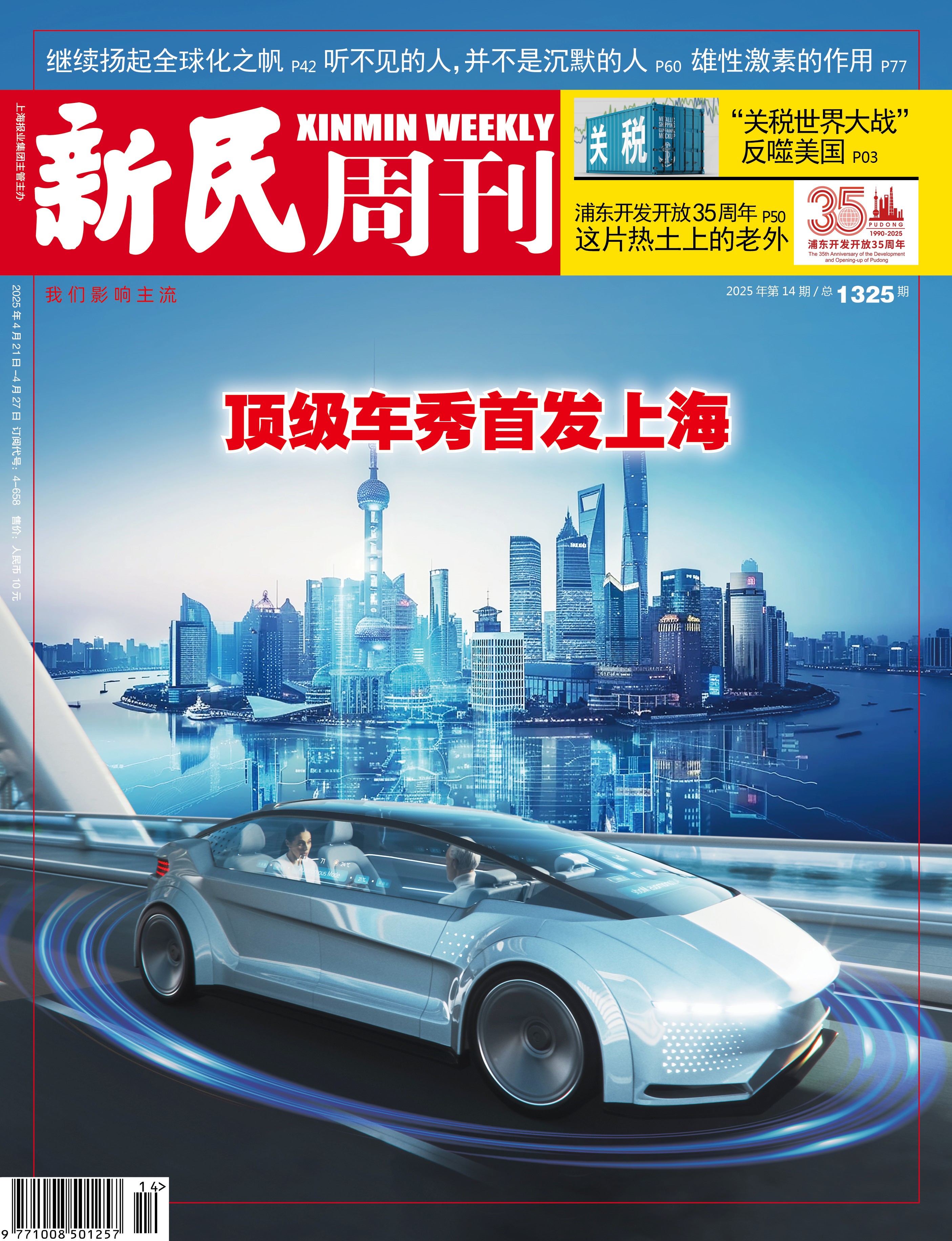34万观鸟爱好者,“对自然的探索与爱纠缠不清”
春暖花开,处处生机盎然。越过寒冷冬季的鸟儿,再次活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2025年4月初,演员李现到北京的公园观鸟、拍鸟,被许多人发现。之后相关话题上了热搜,公众发现原来“观鸟”这件事有这么多人喜爱。根据《2023年中国内地观鸟爱好者和观鸟组织本底调查报告》,国内已有超过34万观鸟爱好者。
观鸟耗费时间,需要耐心,有时在野外的时长难以预估;观鸟也要花钱,无论是相机还是望远镜,有些价格不菲。但观鸟带来的快乐同样难以复刻。种类万千、姿态各异的神奇鸟儿,带给他们另一种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中国,做一次“鸟口普查”
中国大约有34万观鸟爱好者。人的数量有了统计,那么鸟呢?在中国,大概可以看到多少种鸟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想要精确回答并非易事。
按照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院长、鸟类学家刘阳教授主编的《中国鸟类观察手册》,2020年10月之前在中国境内有记录的鸟类物种,共1489种。而根据《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的记录,全国鸟类共有1505种。可以认为,在我国境内已经有超过1500种鸟类被记录。
尽管在鸟类物种多样性上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统计,但鉴于鸟类自身的习性,这些鸟类的种群数量不会一成不变,而随着气候和环境变化处在波动中。为了对中国的鸟类开展长期的、持续性监测,刘阳教授团队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阙品甲团队合作,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了中国繁殖鸟类调查(China Breeding Bird Survey,CBBS)的公民科学项目。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刘阳告诉记者,正式调查将于5月的第一周展开,从清晨开始,直至中午前结束。在鸟类的繁殖期内,使用一套标准化的调查方案,调查一个城市的繁殖鸟类。
作为全国调查的第一年,CBBS今年调查的城市包括广州、深圳、成都、北京和上海。届时在调查开展期间,上述城市会被划分为10公里×10公里或5公里×5公里的网格,这些网格就是调查样区。每个样区内又会设置10个至15个调查样点,调查人员需要记录在样点看到、听到的所有野生鸟类。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鸟类并不是只依赖眼睛看、靠相机拍,还要靠耳朵听。这与平时观鸟“加新”(指观察到新的鸟儿)的体验不同,要求调查员得熟悉当地常见鸟的鸣叫声。因此,在正式“上岗”前,调查员们还需要接受多次培训和考核。
“这项调查在2025年开启,但早在2021年我们已经开始酝酿。在国外和中国香港,类似的网格化调查相对经验成熟,我们有学生去进行了相关的调研;近年来,阙品甲老师的团队在成都也开展了一些以标准化的方法‘数鸟’的调查活动——成都繁殖鸟类调查。”刘阳说道。
谈及CBBS为何在今年正式开启,刘阳表示,CBBS并非一项“纯科研项目”,而可以被视为一种由公民参与的“鸟口普查”,因此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
据中国观鸟记录中心负责机构朱雀会对中国大陆观鸟人群的调查显示,2017年观鸟活动影响人数超过14万人次。这一数字在近年持续高速发展,到2023年总数量已经实现了成倍增长。
《中国鸟类观察手册》从2021年出版至今,已经销售了十多万册。作为可能是中国第一代观鸟爱好者,刘阳意识到这个数据反映出中国的观鸟爱好者已是相当庞大的群体。
观鸟爱好者们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志趣,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参与科研项目,帮助科学家收集数据。截至4月下旬,五个城市报名CBBS的调查员已经超过了500人。
与之对应的是,考虑到公民参与的可行性,CBBS将城市作为主要的调查地。据刘阳解释,城市人口更多,观鸟爱好者更集中;公民科学家们时间有限,关注城市中的鸟类更方便;城市环境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
作为CBBS广东团队核心成员,在深圳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工作的戎灿中告诉本刊,如今中国的大城市中已有许多观鸟团体。此次调查的前期筹备,他负责的一项工作就是尽可能将这些团体连接起来,让更多人参与。

上图:资深“古法观鸟者”戎灿中正在用望远镜观鸟。受访者供图
过去在一些报道和宣传中,常常能见到“某地出现一种鸟,意味着当地环境明显改善”的说法。但是在刘阳看来,这样的说法并不严谨,“我们不能以单一物种短暂的出现或消失来评判某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变化,因为这当中会有偶然性”。
因此按照计划,CBBS的调查将持续3年。发起者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调查。调查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开展,时值许多鸟类的繁殖期。大部分鸟类在繁殖期都会占区营巢,活动范围比非繁殖期更固定。在此时展开调查,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
成为一名观鸟者
20世纪90年代,刘阳还是一名中学生时,已经爱上了观鸟。他记得当年在城市中的观鸟爱好者,多是一些鸟类学工作者。
“学术化”,也许是中国早期观鸟爱好者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在刘阳的观察里,那会儿大家“一板一眼”,观鸟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在中国,观鸟在近些年才成为热潮。但回顾观鸟这件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已有两百多年。《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认为英国观鸟活动的鼻祖是18世纪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怀特在工作和生活的教区长期以“古法”(裸眼)观鸟,细致记录物种的习性、迁徙行为。“birding/birdwatching”这个专有指称在19、20世纪之交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大众观鸟潮流兴起的标志。
20世纪初期,在华的欧美人士把观鸟活动带入中国。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英国人威尔金森(E. S. Wilkinson)和成都的戴珍等人开启了国内观鸟先河。
除了观鸟爱好者数量迅速增加,刘阳也见证了这一群体在中国更加细致的变化。观鸟从最初充满学术和专业气息,到如今变得愈发多样。
有人执着于记录每一种看到的鸟类,并逐步成为一名“公民科学家”,也有人完全出于闲情,只为欣赏鸟儿;有人为了观鸟,跑遍祖国大江南北还不满足,想要去国外观鸟;也有人专注于身边环境,希望穷尽自己所在城市的每一种鸟;有人爱看水鸟,也有人喜欢猛禽;还有人不满足于观鸟、拍鸟,他们还会去户外录下各种鸟鸣,然后逐一识别。
随着观鸟、拍鸟人群的不断壮大,人们的观鸟设备也不断升级。据朱雀会2024年调查显示,拥有长焦镜头的观鸟爱好者占比超过70%。除了数码相机和长焦镜头,望远镜也是最常见的观鸟设备。许多依赖眼睛观察的“古法观鸟者”,离不开望远镜。入门级别的望远镜,价格通常不超过1000元。以蔡司等为代表的国际品牌望远镜,有些售价近万元。
作为一名资深观鸟爱好者,戎灿中一直坚持“古法观鸟”。距今约10年前,戎灿中在大学期间爱上了观鸟。毕业后从事城市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让他有更多机会到户外,也把观鸟的爱好保持至今。对他而言,观鸟并非刻意坚持,而是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
相较于用相机拍鸟,戎灿中更喜欢用望远镜看鸟。“用相机拍的好处在于,事后翻看照片,能够辨识一些细节,获取更多信息。但是用望远镜看鸟时,更能够享受当下,沉浸其中,会看到鸟儿实时的动态行为,感受到它和人类所处环境的关联,也更容易触发我们对鸟类生态的理解。”戎灿中说道。

上图:大山雀在公园的灯柱里筑巢。受访者供图
爱鸟周,很多人在行动
4月7日,2025年全国“爱鸟周”暨“护飞行动”正式启动,主题为“清除鸟网·密织法网·让鸟儿自由飞翔”。由于南北气候不同,全国各地选定的“爱鸟周”时间也不尽相同。在上海,《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中明确每年4月第二周为上海市“爱鸟周”。
今年上海市第44届“爱鸟周”启动仪式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记录“在册”的野鸟种类增至534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5.2%。近年来,上海诞生的大多数鸟类新纪录,也离不开观鸟爱好者的“慧眼”。4月19日,第二十届上海市民观鸟比赛在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圆满完成。
随着观鸟爱好的深入,除了参加观鸟比赛,许多观鸟者都想要为鸟类做些什么。4月初,当李现“打鸟”出现在热搜时,也有观鸟爱好者指出,“打鸟”不应该出现在公开报道,还有人特意撰文讨论这件事。“‘打鸟’这个提法引起了一些观鸟爱好者的争论。许多人认为,拍鸟、观鸟都是中性词汇,而‘打’会有不平等的意味。”戎灿中说道。
事实上,多位鸟类学专家也向本刊建议,提及拍鸟时,尽量不使用“打鸟”,容易引起歧义。
在戎灿中的观察里,近年来国内观鸟爱好者的新变化之一,就是人们对于鸟类保护的理念不断提升。在他看来,以前人们观鸟,可能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现在大家愈发重视保护鸟类的生存环境。比如一些观鸟团体组织活动时,会反复提醒成员,尽可能与鸟保持距离,不要因为观鸟而破坏当地环境。
“对自然的探索与爱纠缠不清”,这是戎灿中的微信签名,源自他喜爱的一位博物学家。在他看来,人类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对自然的喜爱,这正是许多观鸟者坚持的动力。记者|王仲昀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