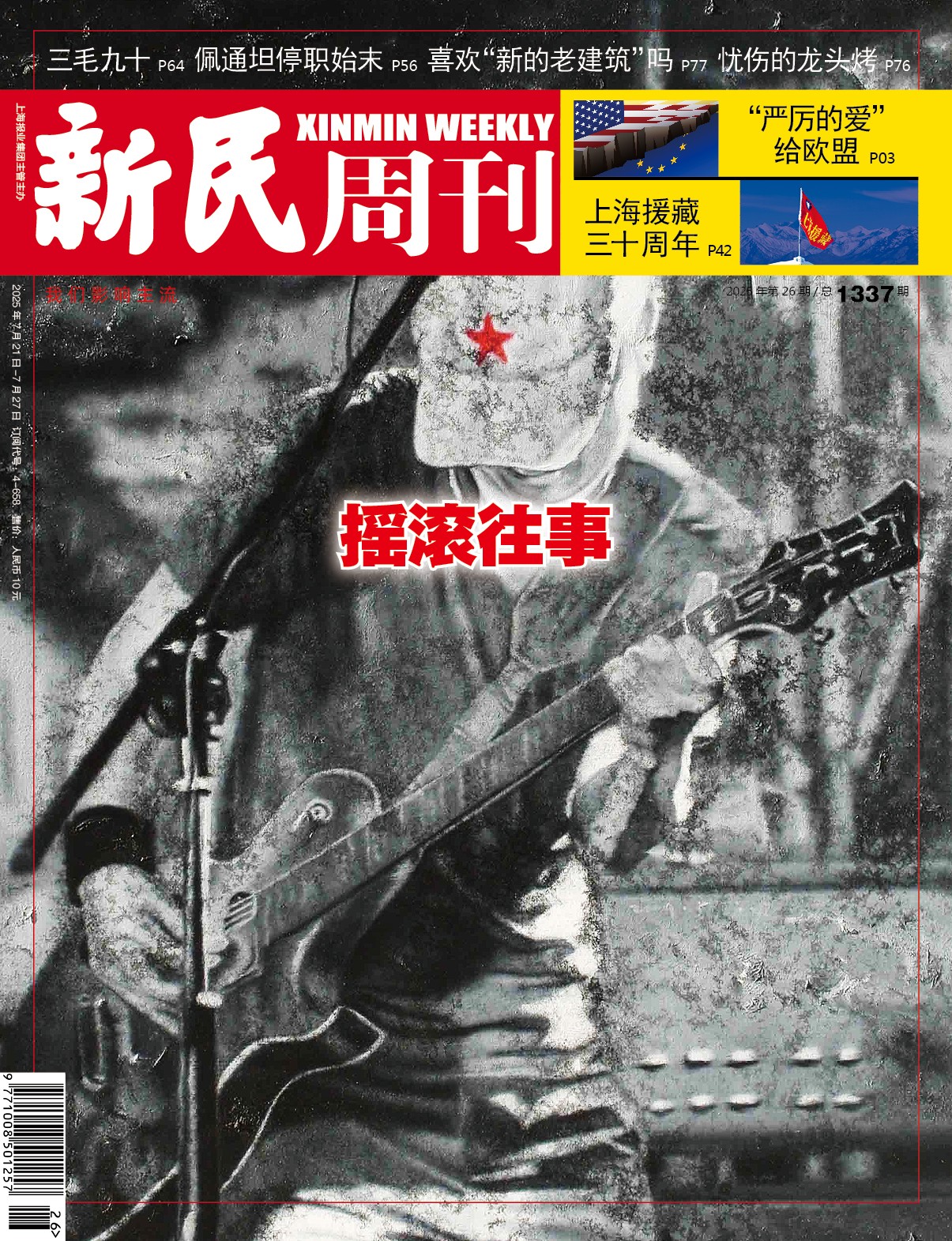志怪文学千千万,何必一直拍聊斋
《聊斋:兰若寺》正在影院放映,而笔者的想法只有一个:拍志怪类影视,没其它IP可以开发了吗?
蒲老师虽难掩猥琐,然确有才气,其原著系“污邪”儿童幼年时期常阅常新的优秀读本不假。而问题在于,再优秀的读本,也经不住被这么一茬茬地盯着同样的点位死命薅羊毛啊。一篇《聂小倩》,到底要整多少出冷饭热吃的戏码?除了《聂小倩》《画皮》《崂山道士》……,《聊斋志异》里若干口味清奇的小众文章就不能深挖深挖?除了《聊斋志异》,《列异传》《搜神记》《酉阳杂俎》《夷坚志》难道不香吗?
请当代文艺工作者暂且放过《聊斋》罢。(P.s. 也请一并放过四大名著、《封神演义》、白蛇青蛇等等。)
传奇故事
《汲冢琐语》是战国时期出土于汲郡魏襄王墓的杂史体志怪小说,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卜筮、梦境、妖怪等异闻,被明代学者胡应麟誉为“古今纪异之祖”和“小说之祖”。
当然,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名气更大。它的一面是地理书,另一面是妖怪志。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内容魔幻精彩,连小时候的迅哥儿都曾为其所深深吸引。
六朝时期,志怪小说有五六十种、近千篇之多,包罗万象、绮丽诡谲,开启了后代文学家们的种种脑洞。其中,干宝的《搜神记》几乎囊括了魏晋之前的志怪小说,好版本值得一生收藏。《拾遗记》《幽明录》《异苑》等亦字短意长,玄妙得趣。人类无穷的想象力照映冷酷的现实,使六朝志怪成为国风“小说”的基石与经典模板。
“唐传奇”的“传奇”,最早见于唐末裴铏的故事集《传奇》,意思是奇异的故事。到南宋时,开始用“传奇”一词泛指唐代虚构性的小说,成为文体分类。作为古代小说成熟期的代表,唐传奇的瑰艳文思为后世提供了数不清的灵感,元明戏曲即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等。
《河东记》《酉阳杂俎》《玄怪录》《独异志》《甘泽谣》……唐传奇里的志怪分支延续了六朝志怪的传统,掺杂佛、道思想,既充斥着怪力乱神元素,亦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并非单纯的猎奇,往往意有所指。《枕中记》的黄粱一梦和《南柯太守传》的蚁巢世界揭示尘世富贵的虚无,《板桥三娘子》让三娘子变成驴子辛劳数十载表露因果报应的信仰,《王知古》用鸟兽精怪都异常畏慎藩镇张直方的剧情曝光晚唐藩镇的专横跋扈……各种“内涵”,自有可笑处、可怖处、可悲处、可叹处。
人怪合一
《夷坚志》书名出自《列子·汤问》:《山海经》为“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洪迈以夷坚自谓,以其书比《山海经》。全书420卷(今仅存206卷),其“浩大工程”,《四库全书总目》称“出于一人之手,而卷帙遂有《广记》十之七八者,唯有此书”。《夷坚志》是宋代志怪小说发展到顶峰的产物,也是《搜神记》以来志怪小说的又一高潮。
《续夷坚志》与《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则皆为《夷坚志》的续作,收录了不少金元时期的神怪、冥应故事,部分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明代的《剪灯新话》因言情志怪、有悖道学而遭朝廷禁毁,在国内流传较少,但此书曾广泛流播于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成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罕见个案(仔细玩味,其实成为古早“顶流”的密码,和短视频时代的一些流行逻辑是相通的)。同时,它开启了后世“剪灯”小说系列,影响甚巨。
清中叶以来,《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这两部志怪小说集广为流传,前者与《聊斋志异》齐名,纪老师点到为止,有章法、有情致。
异物为怪,物反为妖,那些“不正常”“违背理解”的东西,遂变成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妖怪”。害怕、好奇、困惑、厌弃是它们带给人类的观感,但之所以产生上述情绪,是因为妖怪本就是人类的一部分、是某种“反常/对立”心态的外显,是人性的延伸;尽管人类希望与它们划清界限,它们却不断冒犯入侵,有恃无恐。
怪由人生,见怪不怪。真正让笔者觉得难以忍受的,是“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王小波《万寿寺》)。撰稿|安妮
链接:《山海经》
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