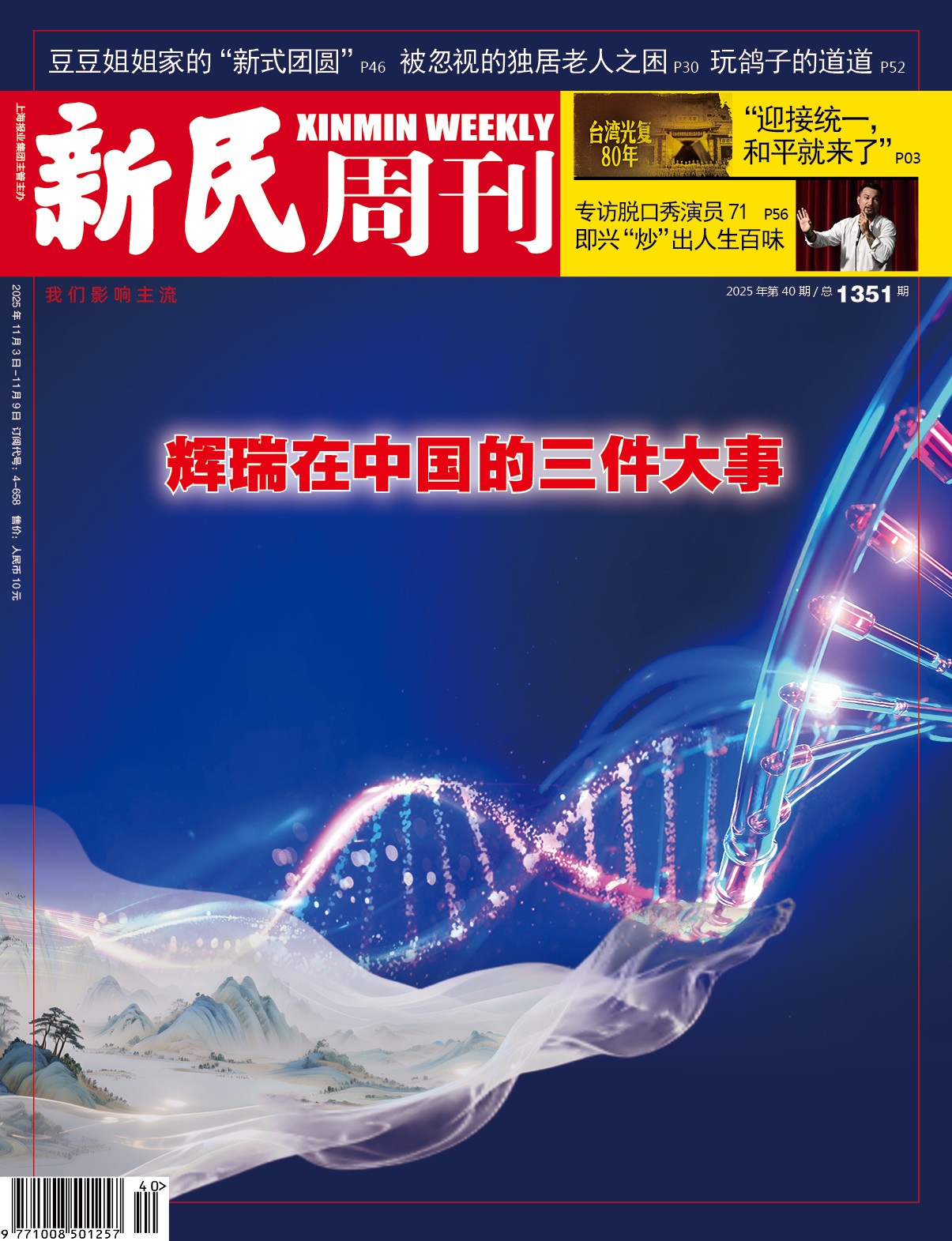中国的“神奇动物在哪里”
秋季里偷闲去南京明孝陵一游,神道上最美的风景,莫过于延绵600米的石象路。红橙黄绿的彩叶树种掩映下,巍峨石兽们或跪或立,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个子略矮些的石兽脊背,都被骑坐或抚摸得溜光水滑,有一些犄角已然破损,大多身上有对称的浅浅圆坑痕迹,似乎曾经被镶嵌了宝石。这些静默屹立的石兽,在一代代人的仰望与触摸中,把历史的温度留在了肌肤纹理之间。
写在石头上的文明史
说起中国的石兽文化,由来已久。
战国到汉代的石兽带着神秘与朴拙。河南南阳城汉画像馆收藏的东汉天禄、辟邪,用整块青石雕成,肩生双翼,昂首向天。那时的工匠用最简练的线条,刻画出神兽内在的力量感。汉代石兽不追求形似,而在乎神完,这种艺术理念影响了后世千年。
南北朝的乱世,反而催生了石兽艺术的第一个高峰。南京、丹阳一带的南朝陵墓石刻,如今仍有三十几处,大多静立在被游客遗忘的角落中。唯有南京仙林附近的萧景墓石辟邪,因为身材敦实样貌神气,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连南京市徽上的神兽都是照着它的样子所画。
这些带翼神兽的造型,明显受到波斯、希腊艺术的影响,见证了那个时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来到唐代时期,石兽走向了写实与雄浑的巅峰。乾隆皇帝曾为昭陵六骏题诗赞颂:“石马嘶风唐陵前,犹忆当年百战场。”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昭陵六骏,虽为战马浮雕,却代表着唐代石兽雕刻的最高成就,被鲁迅先生誉为“前无古人”的创作。其中“飒露紫”身上还能看到丘行恭为它拔箭的瞬间,人与马的情谊定格在石头上,让冰冷的石头有了体温;只恨百余年前飒露紫和拳毛騧被贼子所盗流失海外,如今只能从复制品中一窥风姿。
宋元以后,石兽逐渐从皇家走向民间。山西晋祠博物馆收藏的宋代铁狮,已不见唐代的凶猛,多了几分温顺可爱。
而到了明清时期,北京故宫太和门前的铜狮,更成为权力与秩序的象征,其造型规范却失去了早期的野性活力。
石兽家族的面孔与灵魂
行走在中国大地,你会分分钟与庞大的石兽家族邂逅,它们各司其职,各有性格。
狮子无疑是石兽中的王者。作为佛教护法兽随佛教传入中土,狮子逐渐取代了本土的虎成为门卫首选。太和门铜狮右为雄,足踏绣球,象征一统江山;左为雌,抚弄幼狮,寓意子嗣昌盛——这一规制成为明清官式石狮的范本。
麒麟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祥瑞之兽。《宋书·符瑞志》描述其“麋身而牛尾,狼颈而一角,黄色而马足”,实际上历代造型千变万化。北京法海寺博物馆前的明代石麒麟,已完全形成鹿角、龙鳞、牛尾的复合形象,成为仁政的象征。
除了担当“祥瑞”的重任之外,一些石兽还有着有趣的双重身份。貔貅因其“有口无肛”只进不出的特性,从古代的军队象征变成了今天的招财瑞兽。迷你石摆件用来庆贺开店最合适不过,但千万不要作为生育的礼物赠送以免被人打出门来……
而赑屃——龙之六子,因善负重而成为碑座的首选。它的长相让人很难不怀疑它的妈妈是乌龟——苏州文庙内的宋代石刻天文图就是由赑屃背负,龙和龟能留下爱情的结晶,科学与传说也能够在此奇妙地结合。
石头坯子总比血肉凡胎坚韧顽强,更经得起岁月的反复摩擦。石兽们见证了太多王朝更迭、战火硝烟,也见证了寻常百姓在它们身边生息繁衍。河北曲阳北岳庙博物馆前的元代石狮,背上至今留着抗日战争时的弹痕,却依然昂首挺立,如同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
近日,“百兽献瑞——中华历代石兽艺术展”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以历代石兽珍品为导引,为公众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石刻艺术之旅。或许当你身临其境,会更加理解它们为何能穿越时空打动我们——我们中国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它们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又往何方去?它们并不是中了石化咒,生来就是石头,又不具备大圣和宝玉的种种灵通;但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它们沉默存在的本身,就是一部值得细读的石头记。撰稿|姚佳琳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