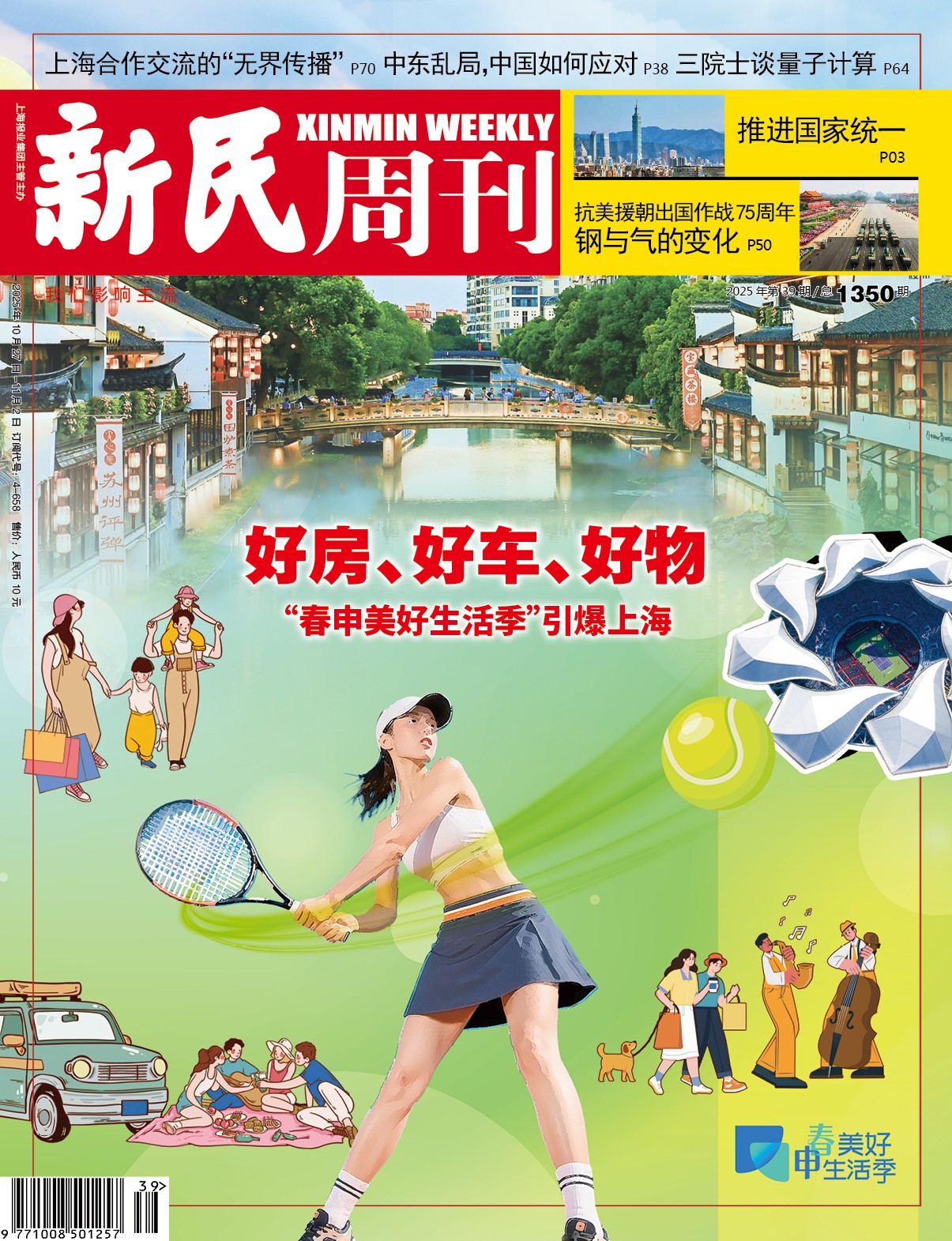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之战与时代传承
2025年,正值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这场始于1950年的战争,不仅是新中国军事上的“立国之战”,更是外交上的“奠基之战”——它发生在冷战两极格局的初建期,塑造了新中国早期外交的核心逻辑,也为后续数十年的外交策略埋下了历史伏笔。
75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从“两极对峙”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交舞台从“被孤立”变为“世界舞台中心”,但不变的是 “独立自主” 的初心、“反对霸权” 的立场、“团结发展中国家” 的策略。它所塑造的外交基因——对主权的坚守、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依托,始终未变。
2025年8月底,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外交史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几十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回顾新中国早期外交的实践逻辑,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脉络,为应对当前国际挑战、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上图:2024年9月30日,辽宁丹东鸭绿江中朝友谊桥风光。
两极格局下的生存抉择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球已形成鲜明的两极对峙格局。美国凭借二战后的超强实力,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将新中国视为“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还联合西方盟友对中国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在东亚,美国扶持日本、韩国构建 “反共防线”,并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主导的 “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中国列为重点禁运对象,阻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往来。与此同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虽对新中国表示支持,但其“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明显,试图将中国纳入苏联主导的阵营体系,在援助中附带政治条件。
面对“夹在美苏之间”的生存困境,新中国作出“一边倒”的外交抉择,即坚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与工业建设支持(后续落实 156 个工业项目),为新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关键支撑。
多位参会专家纷纷表示,这一决策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选择,而是基于当时现实安全与发展需求的理性判断——通过与苏联结盟,新中国有效缓解了美国的战略压力,为东北工业基地(新中国初期工业核心区域)争取到安全缓冲,同时获得了工业化起步必需的技术、设备与资金。
但“一边倒”绝不意味着放弃主权独立。新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始终坚守“不被大国操控”的底线。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0—1953 年),苏联曾提出 “联合指挥志愿军”“共管中国东北铁路” 等要求,均被中国坚决拒绝;在战场战术决策上,中国始终坚持以志愿军为主体,苏联仅提供空中支援而非直接干预指挥。这种“既合作又独立”的态度,打破了传统阵营外交中“大国主导小国”的惯性,为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念奠定了最初实践基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系教授马建标在“遏制冷战”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新中国并非被动卷入冷战,而是主动以抗美援朝遏制冷战向亚洲蔓延。美国若占领朝鲜半岛,将形成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冷战的战火可能进一步烧至东南沿海,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将无立足之地。”从这个角度看,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以战止战”的生存策略,通过军事行动打破美国的战略威慑,为新生政权争取到宝贵的安全空间。

上图:1954年4月26日到7月21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正数第三排右三)出席了会议。
多边博弈的开端
抗美援朝虽以军事行动为核心,但背后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多边博弈。新中国在尚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被西方孤立的背景下,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协调”“亚非拉国家争取”“国际规则塑造”三条路径,开启了多边外交的初步探索,为后续万隆会议的突破与国际组织互动积累了经验。
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平等博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新中国并非被动接受苏联的话语主导,而是通过积极参与阵营国际组织(如世界和平理事会、经济互助委员会),争取平等话语权。例如,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中国将抗美援朝的“反侵略”立场转化为阵营内部的共识,通过宣传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正义性,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与支持。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原所长宫力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新中国外交重心向亚非拉的转移,并非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而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就已埋下伏笔。“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关系开始走向缓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走出去’的外交方针,为后来万隆会议上争取多数支持奠定了基础。”
抗美援朝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意识形态与外交立场的较量。当时的亚非拉国家多为刚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霸权主义”“殖民压迫”有着天然的警惕。新中国在战争中展现的“反侵略”立场,与亚非拉国家的诉求形成共鸣。中国在战争中始终强调“抗美援朝是反对美国干涉朝鲜内政,而非反对朝鲜人民”,并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平台,向亚非国家宣传中国的和平主张。1955年万隆会议上,埃及、印度等国对中国的支持,正是源于对中国“反殖民、反霸权”立场的认同,而这一立场的形成,与抗美援朝的实践密不可分。
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通过塑造“和平规则”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1953年,中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首次倡导“谈判而非战争”的争端解决方式;同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抗美援朝中“反对侵略、尊重主权”的立场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这一规则的提出,正如宫力教授所言,“是新中国多边博弈的关键突破——它跳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和平共处’为核心,为亚非拉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强权政治’的国际交往模式”。
后来万隆会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为“十项原则”,正是这种规则塑造的延续,标志着新中国从“军事博弈”转向“规则博弈”,在多边舞台上逐步打破西方孤立。上世纪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国与一大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建交,形成 “第二次建交高潮”,彻底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对华孤立圈”。
1963 年中国提出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强调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这些规则创新逐步形成中国外交的独特标志,不仅为中国赢得亚非拉国家的广泛支持,也为后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积累了话语资源。
历史遗产与当代启示

上图:5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一列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列车驶出德卡鲁尔站(无人机照片)。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是中国和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连接雅加达与万隆。万隆因1955年召开亚非会议而著名。
抗美援朝75年来,其外交遗产始终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早期外交实践积累的经验,不仅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外交格局,更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历史遗产,为当代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启示。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趋势,从冷战结束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基因始终未变,同时根据时代需求不断创新发展。
中国始终将国家主权与安全置于首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集团。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定海神针”。这一传统在后续外交中不断延续: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打破苏联控制,到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再到新时代应对中美博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独立自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核心。
这一遗产在当代中国外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对当前中美博弈、国际秩序变革的复杂形势,中国始终坚持 “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形势自主制定外交政策”,既不与美国搞 “新冷战”,也不与其他国家结盟,而是奉行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的伙伴关系外交,在全球治理中保持战略自主。
反对霸权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立场”。马建标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遏制了冷战向亚洲的扩张”,这一“反霸权”立场成为中国外交的长期坚守。75年后的今天,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形式虽从军事扩张转向科技封锁、规则霸权(如芯片四方联盟、印太经济框架),但中国反对霸权的立场始终未变——通过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安全”而非“集团安全”)、全球发展倡议(助力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中国延续了抗美援朝“以和平促发展、以合作反霸权”的逻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动力。
建国初期在多边舞台上的探索,为中国外交积累了“通过多边机制实现共赢” 的经验。从万隆会议到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逐步认识到多边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多边平台,中国可以打破单边主义封锁,凝聚广泛共识,推动国际规则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这一遗产在当代全球治理中尤为重要——面对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等全球性挑战,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G20、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记者|陈冰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