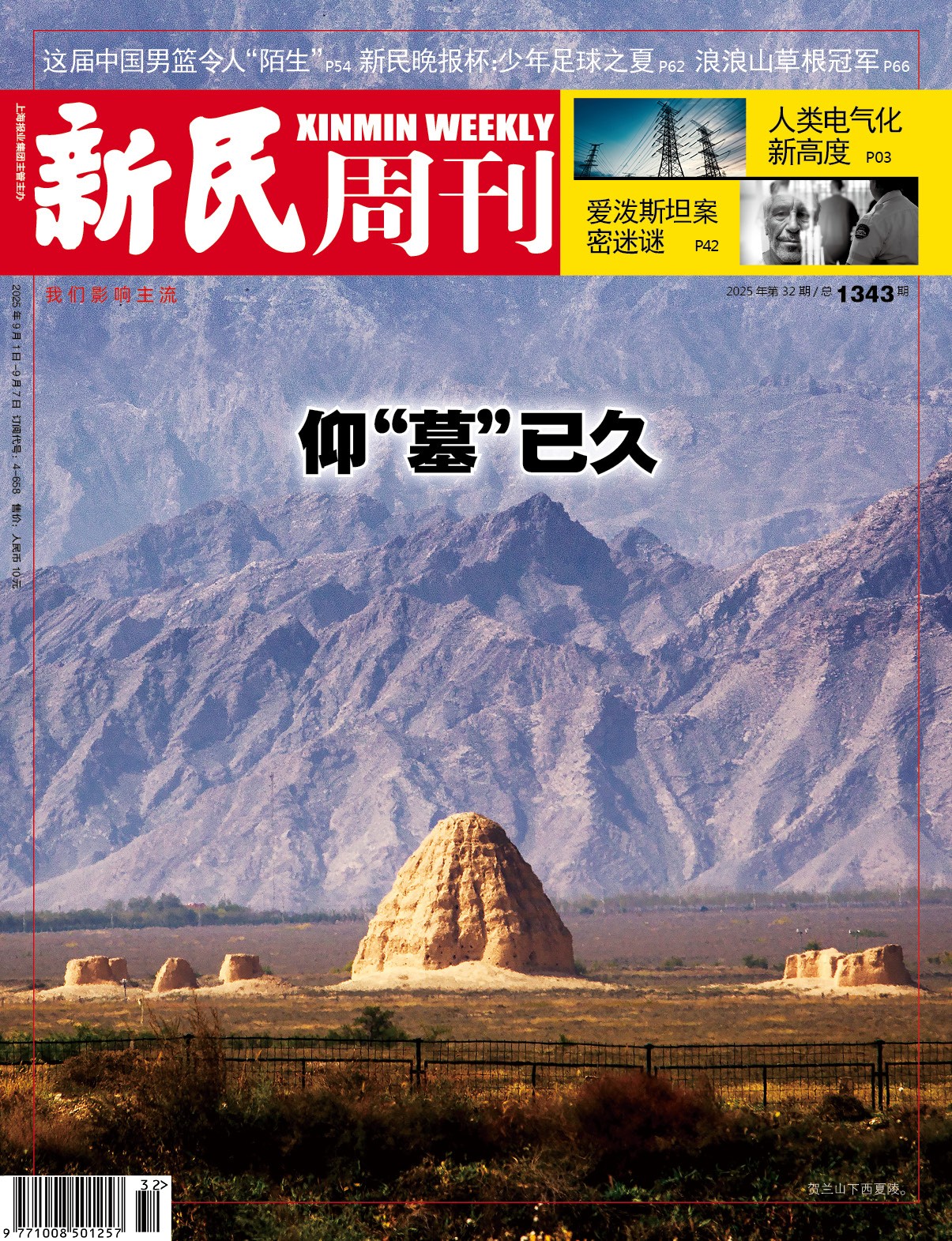专访艾热:说唱不是“没文化”,它的名誉对我很重要

时隔6年,艾热终于要发布个人全新专辑了。熟悉这位说唱歌手的人,会在近几年各种音乐类综艺见到他。展现自己跨界和多样性的同时,突然有一天,艾热觉得参加综艺好似“在上班”。一旦上班,有了班味,就不好玩了。
“音乐玩家”艾热选择暂时退出。他只想用音乐说话。
艾热,全名艾热帕提·艾尼玩,当下享誉中国说唱界的歌手,被许多“90后”“00后”喜爱。这位出生于1993年的说唱歌手,曾夺得2018年《中国新说唱》全国总冠军。那一年的节目里,艾热原本被淘汰,却在复活赛环节“以一敌五”,成功复活,最终拿下冠军。他在节目里唱,“中文说唱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后来,他又先后两次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节目里夺冠。
近年来,已走到中文说唱版图中间的艾热,逐步从说唱圈走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2023年、2024年,他连续两年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另一位说唱歌手王以太合作《别怕变老》等歌曲,成为年轻人当中传唱度极高的“婚礼三部曲”。
艾热的全新专辑即将发布,他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这是一场“严重超时”的访谈。原本计划一小时的采访,最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反差感,这是《新民周刊》记者和艾热见面聊天之后最强烈、最直接的感受。以往的印象里,艾热很躁、很奔放。当天的采访,他面对记者的问题,语速不快,安静地讲述,向人展示了自己的另一面。
新环境、新专辑
《新民周刊》:从去年开始,你们一家人搬来上海生活。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从新疆喀什,到之前你所在的深圳,再到上海,这种生活环境的变化,对你新专辑的创作有影响吗?
艾热AIR:生活在不同的温度、气候条件下,人们都会对音乐有不同的感知。生活在推动我去不断地更换自己的生活环境。我和我的爱人都是随遇而安的人,我们觉得只要自己感到舒适,无论在哪儿,没那么重要。
对我来说,在所有中国的城市当中,没有比上海更好玩的了。上海这地方充满了未知,非常有趣。它就像我们玩沙盒游戏,城市里总会有很多等待解锁的问号。等你跑过去,又出现了新问号。小小的一个唱片店,一家有趣的小酒吧,一个小餐厅,到处有一种探险的乐趣。
《新民周刊》:2021年,你和王以太的合作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至今在互联网上评价非常好,《别怕变老》这些歌被年轻人称作“婚礼三部曲”。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些歌认识你。这些成绩,会对目前以及未来的创作有压力吗?
艾热AIR:这事跟看电影一样。导演拍不同的电影,也会有不同的票房预期。每个做音乐的人,每一次做出一张专辑,其实也是在试探自己与这个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究竟能不能够达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
我和以太的专辑里,能够拥有一些相对脍炙人口的音乐,那是因为我们的磁场正好紧密相吸,产生了很强大的能量。那一年,我们的音乐,配合着当时的综艺环境,加上在节目过程中得到了很多额外的辅助和加持。

上图:艾热曾夺得2018年《中国新说唱》全国总冠军
两个人的力量,肯定要大于一个人。尤其前两年,我和以太可能刚好属于“当打之年”。当时聚合一切,迸发出来的能量场,跟现阶段我个人专辑的能量场肯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不去关心市场的反馈,反而不正常。这些反馈不能算是压力。
《新民周刊》:很多人好奇,说唱歌手们日常如何去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你之前采访时提到,高中时会一直在笔记本上写词。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艾热AIR:所谓说唱歌手写歌词,其实都差不多,通常以一个韵脚为开头去进行创作。想到一个开心的韵脚,我们先用纸笔把它记录下来,再形成有逻辑的语句。以前我上学的年代,处于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阶段,不像现在初中生都可以拿到智能手机。
直到做这张专辑,我依然努力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我觉得笔和纸可以让人回到一个安静的状态。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语言表述能力很匮乏的人。或者说通过语言表达情绪,我总觉得不够精确,所以我享受创作,享受写词,可能现在不太会再用纸和笔写歌词了,这个习惯转移到手机的备忘录里面。
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手机备忘录写“书”,写我自己的一个类似散文的随笔。我这个备忘录的名字就叫随笔。前段时间看,已经写了有一万多字了。这一万多字,都是小篇的、很私人化的一种表达。比如说有一句话:我要当爸爸了。这就是我知道自己要当爸爸的时候写的,我写下来当时所有的感受。
然后你看,这有一篇,主题叫立场,我想讨论没有立场算不算立场。
还有一个主题:坐在北京的高铁上,2022年12月18日。从这个场景,想到自己第一次来北京,然后身边有谁,然后当时是什么样。
这一切都很私人化。当我有一天决定要把它发表出来,真心想把它变成“书”出版,肯定是我的脸皮已经足够厚了。
《新民周刊》:距离你上一次发专辑,已经将近6年了。你这两年参加了各种综艺。为什么想在今年发新专辑?
艾热AIR:没出专辑,就是因为一直在参加综艺节目,它透支了我的很多灵感。我在综艺节目上演唱的一些新歌曲,其实当时都是在为一张专辑预想去创作的东西,结果就被透支了。因为要拿出一些即时性的音乐,一些新的“狠货”,去跟其他说唱歌手们一块比赛。我发现我最爱的那种东西,被一种很无聊的竞技形式去消耗掉了。
但是当时决定去参加各种节目是有原因的。从2022年开始录制,一直到去年10月。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过程,我真的想要去工作,想赚钱。我要当父亲了,理所当然要给我的家庭更舒适的生活,所以我想去通过这些节目录制,还有做更多的商业性质的一些事情去赚钱。
直到做新专辑之前,我发现自己身体和心理上都有一些暗示:我真的累了,而且有点无聊了。录节目一开始是有趣的。我们肯定是不安分的人,想要尝试各种事情。但是一旦感觉有点像上班了,“班味”有点重了,那肯定要逃避。
金黄色的家乡
《新民周刊》:这些年外界一直传闻,你家里有很多牛羊。当年你去参加说唱节目,为了说唱事业,需要家里面的经济支持。你父母为了支持你,卖掉家里的牛羊。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艾热AIR:都是江湖传闻。我是一个很正宗的、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我父母都是中石油的员工,我妈妈在中国石油工作了30年。我们家一直生活在喀什市的中石油大院里,我从小就这样长大。
《新民周刊》:近两年新疆文旅事业发展很好,你的家乡喀什也一样。提到喀什,你脑海里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馕坑里现打出的馕,刚出炉的羊排烤肉,还是土曼河边的高台民居?

上图:提到家乡,艾热永远最先想到的是喀什的家。
艾热AIR:你说的这些,还是大众或者说游客最熟知的喀什意象。对于我来说,我想到喀什永远不可能是这些东西,反而是我的家。我家里每一个家具的摆置,家里的味道,外婆在阳台做饭的场景。我骑着自行车,跟我的几个小伙伴从土曼河边疾驰而过的剪影。
还有那永远不变的夕阳的颜色。金黄色的夕阳。
在新疆,夕阳的时间很长,而且那个时间段跟内地不太一样。我在上海接小孩放学,这边的夕阳时间跟放学时间基本上重叠。回家的路上,夕阳就结束了。而我们那里可能放学回到家,吃口饭出来,在院子里玩了俩小时,太阳还在,所以那边的夕阳对于我们的影响时间会更长久。
《新民周刊》:近年来新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人,从早先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帕尔哈提,到你和你同时期的说唱歌手,再到现在更年轻的一批人,比如做独立音乐的缺省(Default)乐队。我觉得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现象。新疆独特的生活方式、饮食和语言习惯,对音乐人的创作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语言为例,我观察到,新疆的朋友总是能用那种最直白的话把一些朴素的道理讲明白,就像你之前提到,你妈妈小时候教育你,说“有可以吃的屎,但是有不能吃的蛋糕”。
艾热AIR:这个问题,有见地,是我愿意去聊的。
我不能说语言习惯直接影响了某一首歌,某一句歌词,不是A影响了B这么直接。但是它一定存在,就是A到C之间肯定是经历了A和B的,所以语言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它可以让我换一个视角去思考问题。
新疆的音乐人被看见,我觉得和音乐、艺术氛围在新疆长期存在有关,就像广东省有很多优秀的篮球运动员,离不开广东宏远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像上海的足球很厉害,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青训体系。
新疆是一个party浓度特别高的地方,我们从小就在音乐和跳舞的海洋里长大。每个月、每年,家里至少都会有那么一两次的婚礼、聚会、宴会之类,然后我们就一起聚到宴会厅里,听着音乐,“一言不合”就要跳舞,一定要跳。说实话,再社恐的人,就算他不会跳,也会站在旁边,哪怕就这么拍拍手,假模假样配合一下,每个人都会捧场。给艺术捧场,是一件很本能的事情。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每个人都会把这种唱歌或者说从事艺术,看作一件自然的事情,而不是对传统世俗的挑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氛围呢?对我们来说,自古以来,新疆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同时生活方式上也集合了农耕和游牧这两种传统的生活方式。长期受自然条件限制,音乐是我们那里为数不多的、重要的消遣方式。在沙漠里,在冰天雪地里,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听音乐,享受艺术的慰藉,可以让我们忘却乏味、无聊。
新疆人民也爱丰富多彩的颜色,比如喀什的艾德莱丝绸,颜色选择都很大胆、艳丽。这种艳丽是出于我们过往的生活方式比较乏味,所以要选择一种更加豪迈和开放的心态,去拥抱相对乏味的日常。
新疆太大了。和广袤自然相比,人显得很渺小,什么都不是。作为人类,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如果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跟自然对话,不用很含蓄,音乐、绘画和鲜艳的色彩,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音乐玩家”

上图:艾热在2025嘉亿欣·DUO音乐节
《新民周刊》:去年你在乌鲁木齐的第一场演唱会,邀请了崔健担当嘉宾。之前你还和陈楚生在音乐综艺合作过。之前有一档采访里面你说过,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但是这些年你已经做了这么多的跨界合作,你怎么看和不同的人合作?
艾热AIR:也许是吸引力法则在发挥作用。当你每次有一个意向时,老天爷会把这种惊喜的合作,送到你面前来。我父亲前些年已经去世了,不过他手机号码一直保持着开通的状态,手机彩铃一直是陈楚生老师的《有没有人告诉你》。他的手机用这个彩铃,已经将近20年了。我跟陈楚生老师的合作,也是很玄妙的缘分。
目前为止,我的音乐深受崔健老师影响。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有完整地听完崔健老师所有的音乐。但是在前些年,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突然点开发现,天哪怎么他还有这样的歌,他还有这样的音乐形式。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梦想,成为像他一样的“音乐玩家”,让自己的音乐资源库就像海洋一样广阔,像潘多拉的魔盒充满意外。
《新民周刊》:为什么给自己定位“音乐玩家”?
艾热AIR:目前给自己定位最标准的就是音乐玩家。玩家,就不需要受规则限制,很开放。
音乐人、音乐家、歌手,这些定位我认为都不太准确,还是“玩家”最符合。它可以让我有一种不需要负担的感觉。而且它也分特定的场合,《新民周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愿意尊重观点的平台,所以我愿意用“音乐玩家”这个角色去跟你聊天。但是如果在一个很说唱的场合,我说我自己是一个音乐玩家,听着有点装,所以我愿意做一个说唱歌手,哈哈。
保护说唱

上图:艾热想要表达的亲和力,其实并不是为了彰显个人的亲和力,而是想让大家不要预先设置一层对说唱歌手的障碍和偏见
《新民周刊》:有网友表示,艾热是中国难得的没有任何“喷点”的说唱歌手。他在公众场合的表现,似乎和很多人传统想象中比较张狂、特立独行的说唱歌手不太一样。我也注意到虽然你说自己语言匮乏,但你面对媒体,其实挺会说话的。这是为什么?
艾热AIR:我在保护自己,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不要被无形的伤害牵连。现在是一个属于表达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角,每个人都可以快速得到一个表达的机会,而说唱又是一个特别强调表达和个性的形式。
帕尔哈提老师跟我聊天,他跟我说,有个性特别好,但是过于个性,会伤害到身边的人,波及他人。个性也可以害人。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会说话,或者说语言表达不够尽兴。当我事后发现,我有一些话不够准确的时候,我会不舒服。所以我更愿意把一切放在音乐里,因为在音乐里的表达,绝对经过了冷静的思考。
《新民周刊》:之前耳帝提出,艾热的音乐已经能够和世界潮流接轨了。你有没有类似“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外界对于中文说唱的印象”这种想法?
艾热AIR:我不想让别人对说唱有误解,或者小瞧了说唱,老觉得说唱没文化。当大家愈发把它想象成这样时,它的名誉对我来说尤为重要。
我不敢确保我自己能够让说唱这种艺术形式被普罗大众完全认同,但是至少在我出现的场合,尤其大家或多或少知道我是一个跟说唱音乐有紧密相关的人,我希望可以尽量让它看起来得体一点,稍微冷静一点。
在说唱音乐里我们可以放肆,可以毫无克制地去表达。在说唱类的节目里,我会直言不讳。在那样的场合里,一个属于说唱的节目,有说唱的氛围,我当然可以用这里的玩法去表达我自己,展示个性。但是每当面向更多不太了解说唱的大众,我更希望可以用一种比较随和的方式跟大家聊天,这样才能尽量展示一种亲和力。我想要表达的亲和力,其实并不是为了彰显我个人的亲和力,而是我想让大家在我身上感受到,说唱音乐或者说唱歌手并不都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大家不要预先设置一层障碍和偏见。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