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武戏:无技不惊人,无情不动人
翻开历史,中国电影史的开篇,就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一个“武”字。也正因此,中国电影与戏曲、武侠的联系,成为新兴艺术与传统文化结合与发展的典范。
1905年,当我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用镜头记录下京剧文武老生泰斗谭鑫培扮演的老将黄忠跨马挥刀的形象时,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带有京剧“做打”程式身段动作的默片,居然在百年后生长为一棵参天的武侠电影大树。这种“以动见胜”的叙事方式,无意中也为日后武侠电影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不论故事如何变化,“武戏”与“武侠”的结合,成为了永不过时的审美期望。正所谓“无技不惊人,无情不动人,无理不服人”,从红氍毹上的铁马冰河,到江湖里的刀光剑影,从武林中的拳脚生风,到银幕上的快意恩仇……戏曲与武侠始终在电影的世界里,描绘着中国人心中的侠义思想与精气神,也用武术技巧与程式动作,讲述着一个个属于中国人的好汉故事。

武侠里的戏曲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作为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戏曲集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各种元素,讲究“写意型、程式化与虚拟性”,其核心表现力,即王国维先生所谓的“以歌舞演故事”,在这歌舞之中,不仅有抒情化的载歌载舞的艺术化表现,也包括了糅合武术与杂技而形成的武戏技巧。这种艺术精神恰好暗合了电影艺术最初“默片时代”的艺术风格,即以大量肢体语言与动作来讲述故事,表达情感。也正因此,相比于其它艺术门类,戏曲与电影有着更为相似的特质,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以看到电影与戏曲的紧密关联。
最早的中国电影,由于默片无声的特点,创作者们选择了以动作取胜的武戏作为拍摄对象,银幕动作的热闹和传统戏曲舞台相似,吸引了当时的观众。那时候,电影被称为“影戏”,由此可见,尽管是全新的艺术样式,却始终没有脱离“戏”的概念。基于此,武侠片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电影类型之一,也成了中国独有的影片类型。不同于西方的动作片或枪战片、战争片,武侠电影的出现受到了中国侠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戏曲武戏,以及大量流行于书肆报摊中的武侠小说等各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
在《定军山》后,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和郑正秋合作的《火烧红莲寺》又开创了武侠片的新天地。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成为中国电影最繁荣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邵氏电影公司,开启了以李翰祥为主导的“戏曲片”和以胡金铨、张彻为主导的“武侠片”的时代。戏曲电影的“情爱中国”和武侠电影的“江湖中国”成全了那个时代观众心中的“文化中国”,而邵氏公司以大量的优秀作品,更将武侠电影推向艺术与商业的巅峰。
回顾这段历史,毋庸置疑的是,武侠电影受到戏曲武戏的影响最大。早期的武侠片在演员、动作、布景、服饰以及题材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武戏的影子,不仅在题材、演员、武打动作与表现手法上,戏曲行甚至还为武侠电影提供了专业的“龙虎武师”,指导、完成武侠电影的动作设计与拍摄,这一行业后来发展为专业的电影武术指导。特别是一批身怀绝技的戏曲艺人的南下,更为香港武侠片“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功夫电影带着一股浓烈的烟火气焕然一新地登场了。李小龙的《唐山大兄》和《精武门》将武侠电影的刀剑换成了拳脚,把古代的江湖搬到了现代社会。没有飞檐走壁,只有筋骨与血肉的搏击。李小龙的魅力,不仅仅是将“KUNGFU”带进了牛津词典,更在于他打破了武术门派的壁垒,就像功夫电影本身,既有侠义精神,又融入了现代价值观。后来,成龙和洪金宝将功夫与喜剧结合,创造了无数妙趣横生的场景,让功夫电影从“神坛”走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原来,大侠也可以摔跟头,也能边打边搞笑。这种亲民化的创新,使得功夫电影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武侠片不仅贯穿整个中国电影史,更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形态创作中,至今仍是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重要品牌。
从胡金铨到李安
在武侠片的重心转移到香港之后,以胡金铨、张彻为代表的香港新派武侠电影成为武侠片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别是胡金铨这位武侠电影的宗师级人物,以《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侠女》等新派武侠片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在电影艺术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作品不仅标志着武侠电影的新篇章,更展现了中国电影的独特魅力。更有甚者,凭借着卓越的导演才华,胡金铨还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际影坛上声名显赫的导演。
从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质。在电影画面、镜头语言的运用上,明显带有中国古典美学的特征,这源于他对书画艺术怀有深厚的热爱,从他珍视的《张羽煮海》人物设计手稿中可见一斑,笔走龙蛇之间,造型生动,细腻传神,俨然是一位才情横溢的传统画家。而他对京剧艺术的从小痴迷,则为他后来的武侠创作注入了独特的灵感。

上图:传统短打武生剧目《三岔口》片段。
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涵盖了语言、动作、舞蹈和音乐等多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文武相融的特点。戏词富有文学色彩,通过演员的精湛表演,戏中的角色能够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特别是在武戏部分,肢体语言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使得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戏曲的张力与韵律。与此同时,戏曲武戏中的唱、念部分通常较为简单,仅以白口介绍身份或以几句唱腔表达人物情绪,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舞台上运用戏曲程式技巧来表现矛盾冲突,推进剧情发展,在这方面,无疑《三岔口》中的“摸黑开打”是最为形象与生动的典型。而在武戏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且精彩的高难度程式手段,诸如起霸、走边、趟马、打把子、打出手、攒、荡子等肢体动作,这些纯熟精彩的技巧,充分且生动地展现角色的情感和动作,极具戏剧张力与艺术美感。胡金铨武侠片中的许多武打,恰受了戏曲的启发与影响。特别是从电影中人物的辗转腾挪,服饰打扮以及武打与鼓点节奏的配合上,分明能感受到戏曲传统武戏的深刻影响,这与他自幼喜好京剧,并将京剧舞台的程式动作刻意运用到电影中有关。两者的结合,使得他的作品既充满了书卷气,又不失武林豪杰的侠气,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上图:胡金铨执导的《大醉侠》。
1965年,胡金铨执导的《大醉侠》首次融合了传统戏曲的美学精髓,通过精湛的表演和剪辑,将武侠电影的灵动与创新完美呈现。影片中,演员们准备武打出招时的动作与表情,与京剧演员亮相、开打的架势、身段、神情以及步伐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金铨巧妙地将传统戏曲元素融入了武侠电影的创作之中,使得他的作品既保留了戏曲的韵味,又展现了武侠的精彩。
1975年,胡金铨执导的《侠女》问世,这部作品不仅为他赢得了声誉,更标志着新派武侠电影的崛起。在创作过程中,胡金铨深受儿时听闻的武侠故事启发,将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融入电影之中,使得《侠女》成为了一部既具文学性又富于视觉冲击力的杰作。值得一提的是,《侠女》因其在拍摄和剪接手法上的创新性,荣获当年戛纳电影节的综合技术大奖。这一奖项不仅标志着华语电影开始受到西方电影人的瞩目,更使得胡金铨本人跻身国际电影导演的行列。
胡金铨在《侠女》中的表现,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次震古烁今的蝶变。他巧妙地将武侠世界中积极入世的态度转化为飘然出世的精神境界,特别是通过竹林一役的影像语言,开宗立派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武侠电影创作者,李安导演的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卧虎藏龙》中对于竹林意象的表达,恰是对胡金铨武侠电影最高的致敬与学习。
戏曲和武侠是文化民族符号的显著标志,融入了戏曲艺术的武侠电影,则体现了中国电影对于民族文化符号的独特创造性,既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中国文化的表达确定了新兴的艺术语言。从胡金铨到李安,几十年岁月沧桑,戏曲和武侠之间的水乳交融,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对于民族文化符号的独特创造以及中国民族美学的当代实践。与此同时,在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创新中,又推动着中国电影的国际表达,以求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
“武侠+武戏”
作为不可分割的双生关系,戏曲艺术滋养着一代代武侠电影,与此同时,武侠电影所创造的经典IP,也滋养着武戏艺术守正创新。
纵观历史,武戏是京剧当中与文戏密切相关的独立体系。在京剧的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中,都有冠以“武”字的专门行当,武戏演员包罗了长靠武生、短打武生、武小生、武花脸、武丑、武旦、刀马旦等在内的各个行当的演员,而且不同行当都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代表剧目,数量众多,表演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在传统京剧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
兴起于近、现代的“海派”京剧,在接受传统京剧的同时,也因为地域文化和市场需求的影响发生了改变,朝着讲究“文戏武唱”,追求热烈、火爆、惊险、刺激的方向发展,讲究戏剧冲突与张力,在程式表演与舞台技巧上,有着较多创新。在这种趋势和导向下,以武功技艺表演为主、开打热烈的武戏自然在舞台上占据了更加突出的地位。
有着“大武生”美誉的厉慧良先生,将自己的艺术归纳为“南功北戏”。厉慧良一辈子唱的都是京朝派传统剧目,但南方对于武功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了他。他演《陆文龙》有一个独门绝活,陆文龙使双枪,他将一只枪飞出去,用另一只枪勾回来,配以鹞子翻身的舞蹈,如此往还两次,观者无不称奇。就是这手绝活,当年在重庆,连坐在台下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也忍不住击节叫好。新中国成立后,厉慧良定居天津,地理的便利,让他成了中南海京剧演出的常客。毛泽东见到他,总是不忘当年在重庆看到的那一幕。有“出手大王”之称的郭玉昆,创造了“飞剑入鞘”的绝技。宝剑从前面抛出,从背后接入,百发百中,甚至可以双剑入鞘。南派武生奠基人李春来,在《花蝴蝶》一剧中,从三张高桌翻下,翻腾中从背后抽出腰刀,落地绵软。有“江南活武松”美誉的盖叫天,是南派武生的泰山北斗。他演戏讲究真刀真枪,《铁公鸡》用真朴刀开打,《武松打店》使用真匕首将孙二娘头上的“慈姑叶”叉掉,一同戳在台板上……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曾评价他的表演:“他的形体动作精练到难以形容:生动,灵活,飘逸,刚健而准确的动作构成舞蹈的美,表现出勇敢坚定的英雄形象。就舞姿而论,他无论演什么戏都有其独到之处。刚劲有如百炼钢,也可以柔软得像条绸带子;快起来如飞燕掠波,舒缓之处像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走玉盘,戛然静止像奇蜂迎面。”可见当时的武戏在这些前辈艺人的努力下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绝技绝活,不仅增加了戏的可看性,更成了海派京剧独树一帜的艺术特点。恰如京剧表演艺术家赵麟童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北派是工笔画,我们海派就是泼墨画。夸张、奔放,看海派戏永远不会打瞌睡。”
海派京剧武戏的繁荣,离不开艺术市场的需求与观众群体的喜爱,在这一点上,与武侠电影如出一辙——内容有情节性和趣味性,武打追求效果的热烈、精彩、刺激、好看,适应和满足观众追求愉悦松弛、调节身心等需求。
与此同时,武戏节奏鲜明、冲猛火爆、紧张炽烈、扣人心弦,更加吻合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从观众消费、欣赏心理的角度考察,它也较容易满足观众的兴趣和需求,特别是更容易接近青年观众。因此,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京剧舞台上武行演员仍然是群星灿烂,争奇斗妍。特别是在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平原游击队》《奇袭白虎团》等剧中,均化用传统武戏的程式和技巧进行了新的创造,一方面突破旧程式,一方面为现代戏增添了表演技巧与可看性,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等,都让观众耳目一新。
进入新时期,京剧武戏在观众中依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影响。特别是武侠IP元素的加入,无疑为京剧武戏注入新鲜血脉,也激活了武戏演员的热情与能量。近年来,根据徐克同名武侠电影改编的京剧《新龙门客栈》持续热演,恢复排演的上下本海派京剧《七侠五义》也大获成功,满台的武戏演员闪转腾挪,配合海派京剧特有的机关布景,勾勒出一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惊险刺激的视觉效果,加上引人入胜的剧情,几乎场场客满,一票难求。

上图:史依弘等演员表演京剧《新龙门客栈》。
对于深入人心文学影视IP的改编固然是亮点,而更令观众期待与兴奋的,是“武侠+武戏”的结合——以京剧武戏高超技艺、精彩开打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武侠情结。不仅要在舞台上实现“武侠”与“武戏”更好地融合,还要在增强可看性基础上,进一步深挖传统文化的内涵,展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武侠+武戏”IP的转型成功,一方面唤醒了京剧武戏守正创新、求新求变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也离不开中国人对武侠题材一份特殊的情结。如果说海派京剧兴起之时,所能依傍的武侠文本还多是停留在市井英雄与爱憎分明的传统故事,那么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无疑为武侠文化增添了惩奸除恶、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因而他们的作品也成为影视剧、舞台剧甚至网络游戏反复开采的富矿。归根到底,“技与艺”“情与义”恰是能够让幻想的武侠世界,引发现实社会当代观众共鸣的关键。记者|王悦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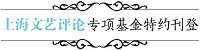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