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第一围合”回归 上海再添地标
11月,“达利×老市府:启程”艺术大展在上海百年建筑——外滩·老市府正式揭幕。展览的开幕也标志着老市府首次全面对公众开放。坐落于福州路200号的老市府,前身为工部局大楼,于1922年建成,距今已超百年。这里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个办公地,也是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之处。
自2015年起,建筑启动保护性综合改造。历经十年保护修缮,如今老市府建筑以全新姿态回归城市,成为外滩城市更新的标志性典范。
近日,《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老市府此次综合性改造的设计方——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在事务所办公室,合伙人陈立缤与建筑师李初晓向记者娓娓道来,讲述了老市府这一段为期十年的修缮保护历程,可谓“既曲折亦有趣”。
十年保护与更新
伍江先生在《上海百年建筑史》一书中写道,老市府这座建筑在建造时,无论其规模之大,还是用料之考究,设备之先进,都堪称上海之最。它既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建筑中极有影响力的一座,也预示了上海的建筑正走向其黄金时代。
倘若要全面地理解老市府在当下进行保护修缮的难度与价值,就必须回到建筑本身,回到它与它建成的年代。
20世纪初,随着当时上海城市的发展,工部局作为公共租界市政最高机构,对于办公空间需求日益提升,建设一座新市政大楼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多方考量,工部局选择了在外滩第一界面之后的这一地块作为新大楼的基地。

上图:历经精细化修缮的主楼梯间,保持了原有历史风貌。
最初的提案在建设一个更高、占地更为紧凑的办公建筑与占地更大而更为舒展的围合型建筑之间摇摆。最终,工部局选择了围合型的市政建筑类型,也为之付出了更多土地费用。
在近代外滩寸土寸金的区域里,每一个由街道围合而成的棋盘式街坊,一般会细分为若干个地块进行开发,建设独立的建筑。在这样的高密度城市肌理中,占据了汉口路、江西中路、九江路、河南中路所围合成整个街区的工部局大楼,更能彰显其核心地位。
后来,工部局建筑师特纳(R. C. Turner)提供了设计方案。1914年,建筑开工建造,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工;战争结束后继续建造,并于1922年建成。建筑整体呈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融入了巴洛克装饰元素。立面采用横纵各三段的经典构图,底层为粗犷的石材墙面,二层以上饰以细腻的水刷石。入口处设有一座宏伟的爱奥尼柱式门廊,上方托起精致的阳台,彰显出庄严与权威。
在20世纪20年代,这座大楼的建设可谓不计成本——耗资接近200万两白银。按当时的银价换算,其造价在当下大约是5.3亿美元,是将近四分之一个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工艺美院建筑遗产修缮与传承中心的蒲仪军副教授认为,老市府大楼结构坚固,用材精美且设备先进。具体来看,从钢框窗到玻璃马赛克瓷砖,再到黑白大理石处理的楼梯,各种用材几乎都是进口而来。此外,整栋建筑都安装了电话系统。“低压热水系统是由伦敦著名的水暖工程师诺布斯先生(W. W. Nobbs)设计,且管道均为英国进口。部分会议室还在20世纪30年代安装了冷气空调。”此外, 目前大楼还幸运地保存着一部百年前的英国SMS公司的铁栅栏电梯,且修缮好可以使用。

上图:老市府大楼修缮,追求一种新与旧的和谐。
李初晓告诉记者,除了用料不惜成本,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巧思,说明一百年前的设计师与工人,也许远比今天人们想象中更加聪慧。“老市府内院的砖墙是混凝土砖墙,砖墙之间是斜切缝。在那个年代,通常是元宝缝、平缝或凹缝。外滩建筑群当中的斜切缝非常罕见。我们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设计师真的很聪明,当雨水从墙上流下来的时候,因为有斜切缝,水不会在缝里面留存,全都流走,建筑得到了很细致的保护。斜切缝的阴影效果让砖墙立面的外观也更美观。”
不过,纵使当年的设计与建造工艺水平高超,用料领先,在经历近半年岁月风霜洗礼后,曾经的“远东第一围合建筑”也逐渐黯淡。1995年,老市府大礼堂因建筑老化、场内积水而宣布停用。
2015年,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下发征收决定,开启了老市府的更新建设。
新与旧,和谐共生
1922年11月17日,当天《申报》在第13版《纪工部局新屋之落成礼》一文里提到,“目下工部局新旧房屋,共占地二十六亩,约值银一百六十万两,就以租界发达之情形论,河南路工部局旧屋不久当有改建之必要云云”。
上文中的“旧屋”即指警署建筑。按照最初设计,老市府本是一处围合式建筑,没有缺口。但由于当年大楼的西南角矗立着公共租界巡捕房,所以大楼在1922年竣工时没有围合。1936年巡捕房拆除,但是在大楼完工后的近百年时间,围合的愿景一直未能实现。
因此,外界有观点认为,此次老市府综合性改造的“最大亮点”,就是新建建筑织补的方式,如何将原本的缺口补上,使新建筑和老楼共同构成一座完整的环形建筑。
补上等待近百年的缺口之外,当记者与陈立缤、李初晓谈及保护与改造中的其他亮点与创新,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要警惕一味地刻意追求“创新”。“我们最大的创新,也许是不太创新。”陈立缤说道。
2006年前后,当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领衔外滩源项目的改造时,业界在修复外立面上发生了争议。到底修旧一点,还是新一点,彼时没有共识。但是到2015年,在老市府保护修缮计划开始时,大家已经没有任何争议——历史建筑不应该修得太新,保留一些痕迹才好;毁坏缺失的部分应得到修补,完整呈现历史建筑风貌。他们追求的是尊重并保留时间在建筑上遗留的痕迹,在和谐的逻辑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建筑的“美感”。
如今在建筑修缮保护时常被提及的一个词汇——“修旧如旧”,或许存在一些误读。基于展现“美感”的前提,要让历史建筑变成“有尊严的体面的老人”,老市府在保护修缮过程中并不避讳“新建”与“扩建”,其追求的是一种“可识别性”:即便是非建筑专业出身的人,在老市府周围走一走,稍加分辨,也能看出哪些部分是新,哪些是旧。
此外,这一次综合性改造在合院的东南角布置了一个独立的新“老市府礼堂”。它与红楼、老市府大楼本体之间形成一种新旧并置的动态平衡。

上图:围合院落中的维多利亚风格“小红楼”经过两次平移,在原址被精心修缮保留下来。
如今,随着建筑工艺越来越发达,历史建筑修缮中一些原本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变得不再遥远。老市府综合性改造的方案设计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可以按照老市府1922年竣工时的模样,将其尽可能地在当下还原。“我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完全复刻一个1922年的建筑,意义究竟在哪里?它在当年是‘远东第一围合建筑’,这是它置身那个时代的价值。如果在今天按照当年的样式重新建造,终究只是高级的赝品。”
献给人民,回归“公共性”
作为上海人,陈立缤儿时不止一次来过老市府。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构成了他最早有关这座建筑的记忆。
在原来的工部局建筑底层的北侧、东南角、西南角,分别开有通往内院的通道。在内院,工部局的万国商团操练厅曾设置在中轴偏南的位置。在操练厅东侧,又贴建有车库以及马厩。原有的红楼建筑则位于内院的西北角。
最初的工部局建筑设计愿景中其实留有内院的规划,但是当上述车库、马厩落成后,空间变得零散,内院的定位随之模糊。
在陈立缤看来,团队当初能够主持这一次综合性改造,或许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设计方案中提出要让内院回归城市空间。如今从街区步入围合区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开阔的庭院广场。在广场当中,两件城市级雕塑——《时间之舞 I》和《背负时间的马》——以柔软的钟表与负重的马匹象征时间的流动与历史的重量,成为外滩的新艺术地标。而伴随着达利艺术展的“启程”,公众也能够在广场上见到一些展览相关的元素。原先逼仄与封闭的内院,在百年后真正与老市府建筑融为一体,展现出不曾有的“公共性”。

上图:大楼幸运地保存着一部百年前的英国SMS公司的铁栅栏电梯,且修缮好可以使用。
如果说“保护”和“新建”“扩建”适用于建筑本身,那么“更新”就达到了更高的层面——空间。“建筑的本质不是表皮,而是空间。如今老市府室外空间的开放性,其价值与意义或许要超过这座存在了上百年的历史建筑。”
如今,随着老市府首次全面向公众开放,它不再是原来相对“神秘”的机关建筑,变得开放、公共,回归城市,服务市民。历经十年,它的再生是为了融入城市,成为上海真正的公共空间。
参考资料:《成为外滩的新会客厅:上海外滩老市府大楼历史环境的保护与再生》蒲仪军、李初晓,《时代建筑》2024年第5期。记者|王仲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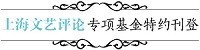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