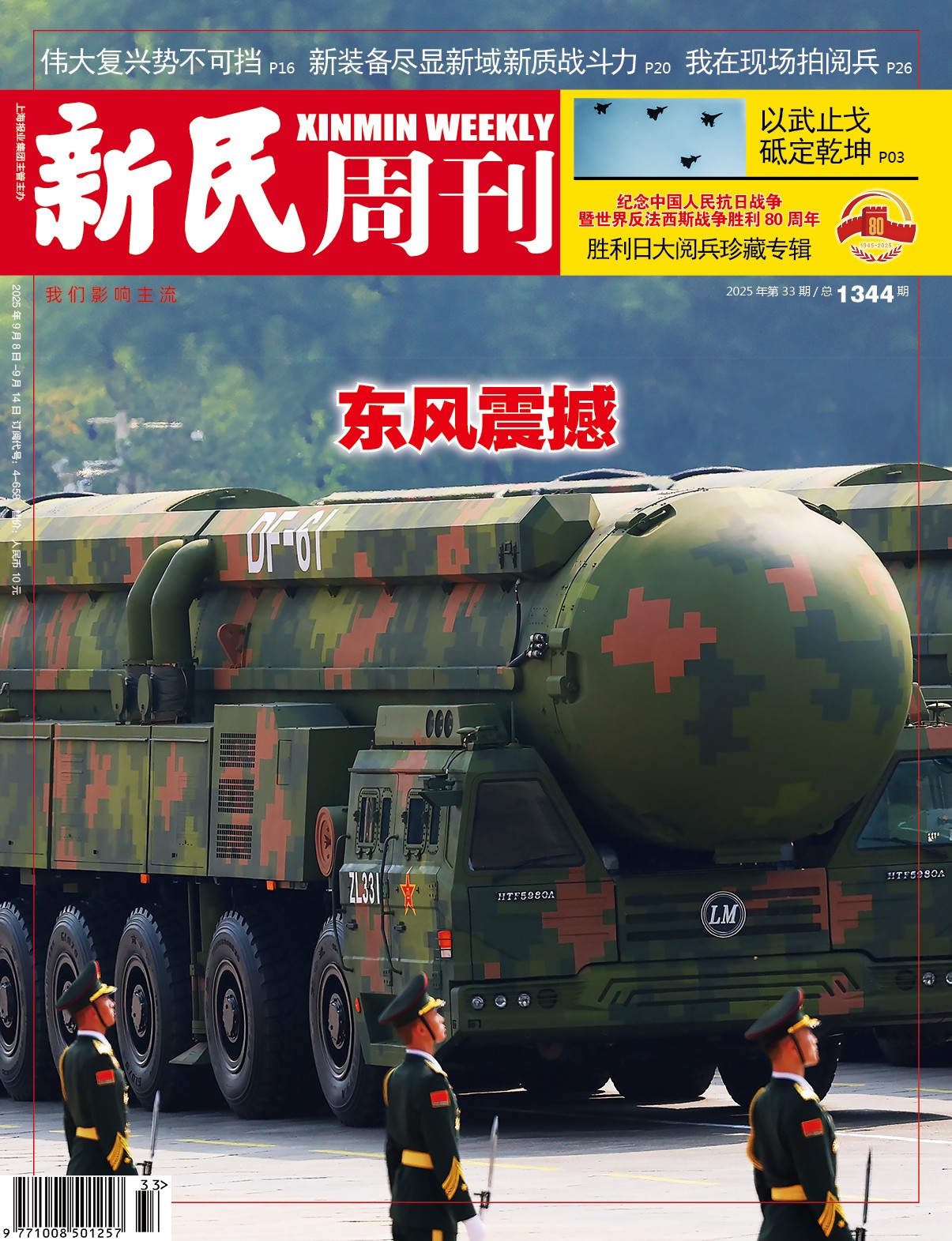暑天话冬笋
暑天之所以话冬笋,完全是我的短视频所致。视频中我叙述了那年的9月中旬去浙江海盐观潮,行李袋里是沉沉的冬笋。评论区里一片哗然。说是时交中秋,哪里来的“冬笋”,显然作者失记了。
其实还真不是“失记”。人们只凭自己的菜场购物经验而错怪了我。事实上,在我们的皖南深山和江西、浙江的深山,冬笋并非只产在冬天,许多地区(比如皖南与湖南)入秋就有了,所以我们回沪探亲前能买到它,事实上笋是一年四季都有的,春笋自不必说,夏有“鞭笋”,秋天的,不妨名之为“秋笋”,只是冬天产的最好且大量上市,大家就叫了冬笋。修辞学上,姑且称为假借,秋笋势弱,便都归了“冬”,被通吃了。
类似现象很是多见。比如哈密瓜,原产鄯善,离哈密还远着呐,故叫鄯善瓜,但因为是哈密王将来进贡朝廷,康熙帝尝了高兴,顺口一叫“哈密瓜”,就一直叫到了今天,怎么也改不过来。再如杭州的著名景点“曲院风荷”,南宋以来一直叫“麯院荷风”,到了清朝某皇一个错题——“曲院风荷”,谁敢当场纠正呢?就一直这么叫了过来。叫久了,大家还觉得比原来的“麯院荷风”更为中听,也更有诗意,便“借”了不还,谁还会提出修改它呢。
2003年我奉命去调查某些商贩制作金华火腿用了“敌敌畏”的问题,至少被我厘清了两个疑问。一、火腿表面的确涂抹了敌敌畏,完全是当地人急功近利所致。传统的火腿制作都是冬天下单,就是要避开苍蝇下蛆,如此则产量受限,要打破产量瓶颈只有春夏秋都下单,然而自春到秋,腌制工场苍蝇不断,而要杜绝苍蝇,只能涂抹敌敌畏。二、金华火腿的传统制作地并不在金华市,而是其下属的浦江、义乌、兰溪、东阳诸县,然而当初这些小小县城并没有力量将自己的产品远销各地,只好统统集中到地区的首邑金华,由金华的大营销商组织力量外销,各地的进货商因为都在金华市进的货,就自然而然地叫出了“金华火腿”。
生活中类似的“张冠李戴”或以讹传讹究竟还有多少,恐怕是多得数不胜数的,近有考证说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并非是瓦特发明的,又说牛顿的万有引力之发明也根本和苹果是否掉下无关,更为众所周知的是,阿拉伯数码实际是印度人发明的,却被归功于阿拉伯人……
细想一下,生活中类似的事是不是太多了?为什么呢?
故而尽信书不如无书。撰稿 胡展奋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